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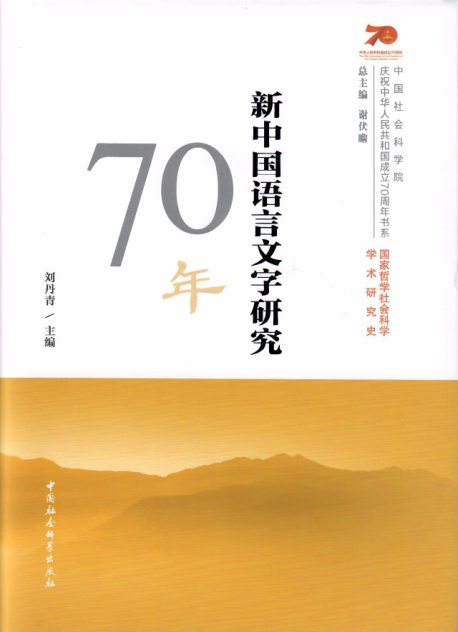
编者按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刘丹青研究员主编《新中国语言文字研究7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中的第九章。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学研究一室王志平研究员。
第九章 文字学研究70年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字学理论和文字学史研究
一、语言学视角下的文字学研究
(一)文字与语言的关系
1.文字学的独立
1906年,章太炎认为“小学”之名不够确切,在《论语言文字之学》一文中正式提出将文字、音韵、训诂三者合为“语言文字之学”,之后章门弟子钱玄同、朱宗莱将自己编写的讲义《文字学音篇》《文字学形义篇》合编为《文字学》一书,这是“文字学”正名之始。从《文字学》的内容来看,包括的范围仍然与原先的“小学”没有多大区别。
与传统的文字学研究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文字学研究显得面目一新,已经脱离了传统“小学”而完全独立,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都与以往有较大不同。最大的不同在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字学研究始终强调语言学视角。王力在《中国语言学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曾经指出:“中国语言学各部门如果有了一点一滴的进步,那都是普通语言学的恩赐。”文字学研究也是这样。研究者都自觉地把文字视为记录语言的符号,把文字学视为研究书写符号系统的一门科学。在研究者看来,文字学的首要任务是研究文字发展和演变的普遍规律,也即揭示文字的性质、功能,文字同语言的关系,文字的类型、构造以及起源、发展和演变的规律,等等。
现代意义上的文字学根据研究对象不同又可划分为若干分支学科。以世界上所有文字为研究对象,研究其结构、性质、分类、发生、演变等共同规律的,为普通文字学,也可称为一般文字学;以记录某几种不同语言的文字为研究对象,比较其结构特点、性质、产生和发展规律的,为比较文字学;以记录某一种语言的文字为研究对象的,则是个别文字学,又称具体文字学。世界上绝大多数文字学研究都属于这个范畴。汉字学也是其中之一。大家习惯所称的“文字学”和“古文字学”多数也是指“汉字学”和“古汉字学”。
在普通文字学领域,需要通晓世界上主要文字,或掌握世界上主要文字资料,范围广,难度大,一直以来以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居多,我国学者多以成果介绍为主,研究心得并不多见。
胜见胜著、陈青今译《ABC的历史》,德国Johannes Friedrich著、高慧敏译《古语文的释读》等译著陆续引进出版,苏联B.A.伊斯特林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也很快介绍到国内(第一版由杜松寿译为《文字的发展》,第二版由左少兴译为《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但是汉字部分往往语焉不详,对中国学者的普通文字学研究起到了激励作用。王元鹿的《普通文字学概论》对世界文字进行了广泛的比较研究,不但揭示了文字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也探讨了文字的本质、性质、分类和归类等一系列问题。
相对于普通文字学,我国学者比较文字学成果略多一些,有些学者把纳西族东巴文字与甲骨文、金文等古汉字对比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相比之下,新中国成立后贡献最为卓著的其实是汉字学研究,成就辉煌。本章即以此为主线,对于1949年以来的文字学研究加以简略介绍和述评。
2.文字与语言的关系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字词关系是语言学研究者首先面对的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些研究者都很注意从这个角度去观察和研究文字现象。任何文字都包含字形、字音、字义三个方面,缺一不可。一些学者如王力《字的形、音、义》、吕叔湘《形、音、义》和李荣《汉字演变的几个趋势》等论著,都很注意汉字形、音、义的特点和相互关系。一些汉字学通论著作如傅东华的《汉字》、蒋维崧的《汉字浅说》、梁东汉的《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蒋善国的《汉字形体学》《汉字的组成和性质》《汉字学》、高亨的《文字形义学概论》等也都很注意汲取普通语言学和比较文字学观点和成果进行编写。
此后,文字学教程一类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如殷焕先的《汉字三论》、姜亮夫的《古文字学》、王凤阳的《汉字学》、杨五铭的《文字学》、詹鄞鑫的《汉字说略》、黄德宽的《古汉字形声结构论》等也均颇有可观。
汉字学的理论建构以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最为突出。此书使用了较多较新的出土文字资料,十分注意以语言学的观点来讨论文字问题。此外,王宁的《汉字构形学讲座》《汉字构形学导论》也注意从构形学角度对于汉字进行了重新解析。
20世纪90年代以后,徐通锵的《语言论》《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语言研究》《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潘文国的《字本位与汉语研究》等论著提出“字本位”理论,对语言文字学界产生了不小冲击。受此影响,孟华的《文字论》等,也对汉语字词关系赋予了新的观察角度。王宁的《论汉字与汉语的辩证关系——兼论现代字本位理论的得失》一文则认为汉字与汉语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符号系统,把“字”移植作为语言单位会造成“字”与“词”的混淆。
20世纪50年代,唐兰在《文字学要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谈谈文字学》二文中提出,“语言学与文字学是不同性质的两门科学”。针对汉字的拼音化方向,唐兰在《行政命令不能解决学术问题》中又提出“语言学重要,文字学也重要,不应该歧视。文字固然反映语言,但不应该仅仅是反映语言”的观点。
1967年,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y)中批评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混淆了语音和文字、言语和书写的区别,以致重视口语声音而贬低文字书写,德里达称之为“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e),即“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与德里达桴鼓相应,孟华的《动机性文字和任意性文字》《符号表达原理》《汉字:汉语和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文字论》,黄亚平、孟华的《汉字符号学》等论著一反众说,提出“文字不是语言的工具而是与语言并行的符号系统,它不是对语言的忠实的记录而是对语言的一种表达方式”,“文字与语言之间不是事实性的因果关系而是思想关系、意义关系,符号关系”,他们将文字定义为看待语言的方式即言文关系方式,强调言文关系是汉字和汉语研究的根本问题,指出要在汉字与汉语的关系中研究汉字或汉语。对于文字与语言的关系提出了新的看法。
(二)汉字的性质与类型
1.汉字的性质
研究汉字的性质,首先要弄清汉字属于哪一种文字类型。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这个问题一度成为文字学研究的热点。人们基本上采用两种方法来给汉字定性。一种是根据汉字字形所能起的表意、表音等作用来为它定性。另一种是根据汉字字形所能表示的语言结构的层次(也可以说语言单位的大小)来为它定性。属于前一种的,主要有表意文字说和意音文字说。在早期,一般都认为汉字是表意文字,20世纪50年代周有光提出来汉字为意音文字说。多数人认为汉字的性质自古至今没有本质变化,但也有人认为汉字的性质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从后一角度提出的观点主要有:商代甲骨文为形意文字周代以后汉字为意音文字说、古汉字为表形文字隶变后汉字为表意文字说。根据汉字字形所能表示的语言结构的层次给汉字定性的,主要有语素文字说和语素—音节文字说。持语素文字说者,一般都承认在单音节词占绝对优势的古代,汉字可以称为表词文字。持语素—音节文字说者,一般也承认那个时代的汉字可以称为表词—音节文字。(裘锡圭、沈培:《二十世纪的汉语文字学》,刘坚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第97—9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7—98页)
2.汉字的结构类型
以往对于汉字结构类型的分析,不脱《说文》、“六书”窠臼。直到20世纪30年代,唐兰的《古文字学导论》才提出象形、象意、形声“三书说”来取代传统的“六书说”。20世纪50年代陈梦家的《殷虚卜辞综述》又把古汉字分为象形、假借、形声三种基本类型,提出了新的三书说。20世纪80年代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提出了“新三书”说,与陈梦家基本相同,但把“象形”改成了“表意”。他认为,表意字使用意符,也可以称为意符字。假借字使用音符,也可以称为表音字或音符字。形声字同时使用意符和音符,也可以称为半表意字半表音字或意符音符字。他还指出了一些不能纳入“三书”的文字,如记号字、半记号字、变体表音字、合音字、两声字。21世纪以来,黄天树的《论汉字结构之新框架》一文提出了“二书”说,认为“六书”是汉代学者创立的关于汉字结构的系统理论,比较切合秦汉小篆的结构类型,但不能囊括各个历史时期所有的汉字结构类型。建议建立一个层级更高的汉字结构“二书”说新框架,把汉字分成“无声符字”和“有声符字”两大类型。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又回到了汉字表意还是表音的二大区分。
(三)汉字的起源
汉字起源问题是汉字学基本理论之一,向来有“八卦说”“结绳说”“契刻说”,“一元论”“二元论”“三元论”等。一般认为“图画”和“契刻”是汉字的两大源头。
新中国成立后,在原始社会时代的遗址里发现了不少刻画或描绘在器物上的符号。学者们对上述原始社会的符号是否是文字进行了很多讨论。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判定这些符号是否是文字应当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标准,这就是看它们是不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这是严格的语言学定义下的文字观。如裘锡圭的《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高明的《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汪宁生的《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等。也有些考古学者持广义文字说,仅是从形体上把某些孤立符号与成熟文字进行比对,并对若干符号进行了“文字”释读。如郭沫若的《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于省吾的《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唐兰的《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字的年代》《再论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和大汶口陶器文字——兼答彭邦炯同志》、李学勤的《中国和古埃及文字的起源》《论新出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等。
按照符号是否记录语言为标准,学术界把汉字起源分为截断众流的两个时段,划分出一个文字/非文字的截然界限,造成了成熟文字与史前图画符号之间的断裂。针对这一矛盾,黄亚平提出了“二次约定”的汉字发生观,在史前的图画与成熟的汉字系统之间建立了一个过渡性符号链条,把断裂的文字演化链条重新联结起来,对于认识文字的性质、史前文字的研究都有理论意义。在此基础上,黄亚平的《广义文字学刍议》《广义文字学研究再议——国外古文字研究带给我们的启示》,黄亚平、白瑞斯、王霄冰的《广义文字研究》等论著突破了“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这一传统观念,提出了“广义文字学”研究的思想。
二、文字学研究与多学科研究的结合
(一)世界文字研究与世界史研究
欧洲语言学的前身语文学(philology),原是研究古希腊、拉丁语等古典学科,其中包括一些文字问题。此外,欧洲也有古文字学(paleography),专门研究解读书写在羊皮、草纸、布帛等上的古代文书。另有金石学或题铭学(epigraphy)是专门辨认保存在古代石刻、碑铭、金属器皿、陶器等上面的古文字的。还有专门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学科,叫Hieroglyph。因此研究世界古文字史必须与世界古代史研究密切结合。
1984年,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林志纯(日知)先生在东北师范大学创办了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填补了国内亚述学(Assyriology)、埃及学(Egyptology)、赫梯学(Hittitology)的学科空白,遵循“读书必先识字”的学术规律,从古代语言文字这一源头入手,为国内高校及研究机构培养了一批能够以苏美尔语、阿卡德语、埃及语、赫梯语、希腊语、拉丁语等古典语言等释读古代原典的研究工作者。其门下弟子如李晓东的《埃及历史铭文举要》,郭丹彤的《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吴宇虹的《古代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经典举要》《古代西亚塞姆语和印欧语楔形文字和语言》,张强、张楠的《希腊拉丁历史铭文举要》,张强的《古希腊铭文辑要》等等,都对世界古典语文学研究作了翻译和评介。此外,刘以焕的《古希腊语言文字语法简说》也对古希腊文字作了简介。
(二)民族文字研究与民族学
1980年,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宗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和组织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献古籍工作者,开展古文字、古文献的学术研究活动。弘扬民族文化,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多、语言多、文字多。除汉族外,已确定民族成分的有55个少数民族,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分布在占全国总面积50%—60%的土地上。5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满族多数已转用汉语外,其他53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有些民族内部不同支系还使用着不同的语言。这些语言分别属于五个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南亚语系和印欧语系。
在我国,除了汉字以外,还有丰富的民族文字,现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满族已不使用自己民族的文字而直接使用汉字外,有29个民族有与自己的语言相一致的文字,其中有的民族使用一种以上的文字,如傣语使用4种文字,景颇族使用2种文字。
我国历史上还存在各民族曾经使用过,但现在己经不使用的文字,这些文字被称为民族古文字。这些文字可以分成几类:一是本民族自源文字,如纳西族的东巴文、水族的水文、彝族的彝文;一种是根据其他文字仿造的文字,如仿造汉字形成的各种方块民族文字,白族的方块白文、壮族的方块壮文、方块侗文等;还有就是后来创制的文字,主要是指政府组织语言学专家、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经过调查研究,先后为壮、布依、彝、苗、哈尼、傈僳、纳西、侗、佤、黎等民族制订的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方案。(邓章应:《西南少数民族原始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5页。参考戴庆厦等《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具体可以参看聂鸿音《中国的文字》(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文字概略》(语文出版社1998年版),王元鹿、邓章应、朱建军《中国文字家族》(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等。
(三)古汉字学与考古学
1949年以前,古汉字学只有少数学者从事研究,因而有“绝学”之称。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学科得到空前发展,研究队伍逐步扩大,成为介于考古学、历史学和语言文字学之间的一个学术领域。目前,古汉字学已有四个学科分支,即甲骨学、青铜器铭文(金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及简帛学。古文字学的迅猛发展,与考古学的繁荣昌盛密不可分。
1973年殷墟小屯南地发掘,找到了殷墟甲骨分期有关的地层证据,这个问题才开始有了共识。而1976年殷墟妇好墓的发现,又导致甲骨分期“历组卜辞”的争论以及甲骨分期两系说的产生,在甲骨学上有很大的影响。近年来,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日益繁荣,尤其是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的出土,又为非王卜辞的学术论争盖棺定论了。
20世纪50年代至今,先后在山西、陕西、北京、河北、河南若干地点发现了西周的甲骨文,尤以陕西岐山、扶风的周原遗址、周公庙遗址所出为多。1953年,在郑州二里岗出土了早于殷墟的字骨;2003年,在济南大辛庄出土了与殷墟同时的卜辞。因此,甲骨学研究涉及的已经不限于殷墟,而且不止于商代了。
青铜器铭文研究与考古学的关系更为密切。1949年以来,考古事业蓬勃发展,重要文物不断涌现,田野发掘为青铜器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重要研究资料。近70年来,全国各地出土了大批青铜器,绝大多数出自墓葬和窖穴,有明确的出土地点与科学的层位记录,有共存的陶器等随葬器物。在众多的青铜器发现中,往往有惊人的发现。如1976年春在殷墟发现的妇好墓,仅青铜器就达200件,这确是重要发现,它为我们重新考虑殷代青铜器的年代序列提供了重要依据,开阔了我们的视野。
西周青铜器发现的地区很多,1950年代出土了许多,如江苏丹徒发现的有宜侯夨簋的一批铜器。安徽屯溪、湖北蕲春、辽宁凌源也都有大量的发现。中原各地发现的西周青铜器,以陕西、河南居多,有的铭文甚至多至二三百字,是重要的历史资料。如1960年陕西省扶风齐家村窖藏出土了28件有铭青铜器,1953—1954年长安普渡村西周墓葬,1956—1957年长安张家坡西周铜器群,河南陕县上村岭西周后期至春秋早期虢国墓群都出土了许多有铭青铜器。近十几年来发现的西周长篇铭文器很多,大部分出在陕西西周铜器窖藏内。春秋的铜器有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青铜器群,河南郏县出土的“郏器”群。战国至秦汉,有洛阳中州路战国铜器,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铜器,湖北随县战国曾侯乙大墓铜器,洛阳西工出土的几件秦代器,河北满城汉墓铜器,甘肃武威东汉墓铜器等。这些大批发掘资料使用现代考古学方法从各个不同方面进行了青铜器研究,如分期断代、器物组合、形制纹饰、铸造工艺等,为利用青铜器资料研究古文字学创造了条件。
简帛发现与考古学关系更为密切。1951年—1954年,在长沙考古发掘中,于五里牌等地的楚墓中发现了竹简,使现代人首次亲见战国简册的原貌。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楚简,1959年甘肃武威磨嘴子汉简,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楚简,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1973—1974年内蒙古额济纳河边塞遗址汉简,1974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汉简,1979年甘肃敦煌马圈湾边塞遗址汉简,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1983—1984年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1986—1987年湖北荆门包山楚简,1989年湖北江陵云梦龙岗秦简,1990年湖北沙市关沮周家台秦简,1990—1992年甘肃敦煌悬泉驿遗址汉简,1999—2002年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遗址汉简,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台秦简,1993年江苏东海尹湾汉简,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简,1993年上海博物馆藏楚简,1994年河南新蔡葛陵楚简,1996年湖南长沙走马楼吴简,2000年湖北随州市孔家坡汉简,2002年湖南龙山里耶秦简,2007年岳麓书院藏秦简,2008年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2009年北京大学藏秦汉简等发现,极大地丰富了简帛文字资料,为简帛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古汉字学与历史文献学
随着新中国成立,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工作也步入正轨,很多古文字与出土文献资料得到了及时的整理与出版。这些古文字与出土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出版为古文字学和出土文献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研究素材。
此外大型古文字丛书如宋镇豪的《甲骨文献集成》40册,刘庆柱的《金文文献集成》46册,曾宪通、陈伟武的《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集释》17册,中国简牍集成编辑委员会的《中国简牍集成》20册,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等的《秦简牍合集》6册,裘锡圭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7册,周晓陆的《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3册,董莲池的《说文解字研究文献集成(古代卷)》14册、《说文解字研究文献集成(现当代卷)》12册,舒怀等的《〈说文解字注〉研究文献集成》3册等也纷纷建成,为文字学研究提供了便利和丰富的文献资料。
敦煌吐鲁番文书方面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英藏敦煌文献》等,资料已经蔚为大观。其他如唐长孺的《吐鲁番出土文书》,陈国灿的《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陈国灿、刘永增的《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柳洪亮的《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荣新江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等吐鲁番文书,以及《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英藏黑水城文献》等黑水城文书,也为有关文字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素材。
(五)汉字学与文化学
汉字是文化的一种,同时也是其他文化的载体。何九盈、胡双宝、张猛的《中国汉字文化大观》提出从文化看汉字、从汉字看文化,分别阐释汉字与农业、畜牧业、车马兵器、天文历法、医药、官制等方面的形义联系,体现了汉字广泛的文化意义。曹先擢等策划的《汉字与文化丛书》,包含何九盈《汉字文化学》、周有光《汉字和文化问题》、王宁等《〈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赵诚《汉字与商代文化》共4种。丛书作者大都还有相关成果。曹先擢的《字里乾坤》《汉字文化漫笔》,王宁的《〈说文解字〉与汉字学》明确把汉字文化学看作汉字学的一个分支。黄德宽的《开启中华文明的管钥——汉字的释读与探索》《书同文字:汉字与中国文化》,黄德宽、常森的《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董来运的《汉字的文化解析》等影响广泛。此外,陈海洋的《汉字文化丛书》,臧克和的《汉字研究新视野丛书》等从历史文化角度着墨颇多。张玉金主编的《汉字中国》丛书共38卷陆续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从中国文化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研究汉字的。刘志基主编的《文字中国》丛书共8卷则由大象出版社陆续出版,也探讨了汉字文化的方方面面。王作新的《汉字结构系统与传统思维方式》探讨了汉字结构系统与传统思维方式之间的关系。王宁的《汉字与文化》、何九盈的《简论汉字文化学》、刘志基的《汉字文化学简论》《汉字——中国文化的元素》等论著对汉字文化学有关理论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对学科建设有积极的意义。
(六)汉字学与心理学
新中国成立后有一些儿童识字过程的心理实验,如杨继本《汉字心理在汉字信息输入编码上的应用》等研究(参见石海泉《汉字字形心理研究概述》,《湖南教育》1988年第11期),但是将认知心理学理论用于汉字研究主要是在21世纪以来才广泛开展起来的。王玉新《汉字认知研究》《汉字部首认知研究》是比较早的专著,内容包括汉字的民族文化特征、汉字构造研究、汉字偏旁化过程、汉字形体的分化、汉字构造方法的演变过程、汉字的简化等,与普通的汉字研究没有大的不同。陈传锋、黄希庭的《结构对称性汉字认知:研究与应用》才开始体现“认知”的理论价值:该书通过9个实验,探讨结构对称汉字认知的加工机制。内容包括汉字认知研究概述、结构对称汉字认知规律的研究意义、结构对称汉字认知研究的目标与计划等14章。曹晓华的《汉字认知的心理机制》是较新的心理实验研究。徐彩华的《汉字认知与汉字学习心理研究》、王永德的《基于留学生认知实验的汉字教学法研究》等也是以实验研究为基础,探索汉字认知特点及外国留学生汉字学习特点。
姚淦铭的《汉字心理学》是建构汉字心理崭新体系的开拓性的学术专著。其探讨的是汉字与心理学相互融合的一系列新课题,解析汉字结构中和汉字运用中的丰厚心理蕴涵,剖视汉字心理的深广层积与民族文化心理的联络缔结。
三、文字学研究的时代背景与历史图景
(一)文字学研究的时代背景
1.文字学研究与马列主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加速发展,出版事业日益繁荣,学术社极成立,科研活动蓬勃展开,为汉语文字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无论是研究的人员和成果,研究的数量和水平,研究的规模和范围,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研究的材料和方法等,均远远超过1949年以前。同时,时代政治的发展变迁,也为汉语文字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想、方法和工具,打上了历史的烙印。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语言学界学习苏联、学习马列主义的热潮中,一些文字学论著中开始尝试把文字学研究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在应用马列主义经典理论研究文字学时也难免有一些生吞活剥的机械之处。同时,由于受到西方中心论的影响,贬低汉字的倾向一度出现。但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字学研究积极吸取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摆脱了过去静止地、孤立地看待汉字的习惯做法,开始从汉字问题各方面间的联系和发展的角度历史地、辩证地看待汉字。如高元白的《汉字的起源发展和改革》、黄约斋(傅东华)的《汉字字体变迁简史》等,都把汉字视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来加以叙述和研究。尤其是梁东汉的《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把汉字的发展变化描述为一个新陈代谢的历史过程,提出了汉字的“新陈代谢律”。可以说,历史地、辩证地看待汉字发展变化,积极探求发展变化的因果和规律,注重汉字与汉字问题各方面之间的联系和影响,这些唯物辩证方法,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汉字研究中得到了较多较好的运用。
2.学术团体的建立与学术中心的聚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字学的发展延续了1949年以前的传统,继续走三条路线:一是文字学理论的研究,二是古文字的研究,三是汉字简化和整理的研究。其中语言文字的改革和规范引起了从上到下的广泛重视,有关工作详见参见王均的《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以及本书的《语言文字工作70年》有关章节,此处不再赘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字学界各个民间学术组织也得到了极大发展。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群众文字改革组织。1991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于更名为中国文字学会,挂靠在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中国文字学会负责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中国文字学报》。1978年12月,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在长春成立。中国文字学会和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作为全国性的文字学界的学术组织,经常举行学术会议,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文字学的发展。中国古文字研究会负责在中华书局编辑出版《古文字研究》。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语言文字应用学术季刊《语言文字应用》创刊,主要宗旨是宣传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政策,研究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开展对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的研究,为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此外,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主办的《中国文字研究》半年刊,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刊物《民俗典籍文字研究》半年刊等,也为文字学健康发展提供了研究阵地。2018年1月,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又与中国文字学会联合主办学术性季刊《文字》,主要发表汉字研究及与汉字相关的研究成果。学会的组织和刊物的出版为文字学事业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基础。
20世纪50—80年代,文字学研究取得了蓬勃发展,文字学与古文字学研究形成了以某些学术大家为核心的若干学术中心,如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郭沫若、张政烺、胡厚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梦家,故宫博物院唐兰、罗福颐,北京大学中文系魏建功、周祖谟、朱德熙,中山大学中文系容庚、商承祚,杭州大学(后为浙江大学)中文系姜亮夫、蒋礼鸿,山东大学中文系高亨、蒋维崧,吉林大学历史系于省吾,四川大学历史系徐中舒,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戴家祥,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孙常叙,等等,老当益壮,各展所长。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专业人才培养从此走向了正轨,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重新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文字学和古文字学课程。1980年,国家建立学位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等,开始恢复招收文字学和古文字学方向的研究生,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很多被耽误多年的青年才俊得以脱颖而出。1984年,国家教委委托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于省吾开办古文字培训班,开设《说文解字》、甲骨文研究、金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等专题课程,又为古文字研究培养了不少后备人才。在新开设的博士点和硕士点中,文字学方向一般归口在语言学专业,而古文字学方向则视招生导师不同分别从属于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等相关专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学勤、王宇信、杨升南、宋镇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公柔、王世民、张亚初、冯时,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黄盛璋,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中国文物研究所文物古文献研究部)于豪亮、胡平生、李均明,北京大学中文系裘锡圭、李家浩、李零、曹先耀(后调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苏培成,北京大学考古系高明、葛英会,吉林大学古籍所林沄、姚孝遂、陈世辉、吴振武、何琳仪、汤余惠,中山大学中文系曾宪通、张振林、陈炜湛、唐钰明,武汉大学中文系夏渌,武汉大学历史系黄锡全、陈伟、罗运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李玲璞、臧克和、刘志基、詹鄞鑫,杭州大学(浙江大学)郭在贻、张涌泉、黄征,南开大学中文系向光忠,四川大学中文系项楚,上海博物馆马承源、陈佩芬、濮茅左、李朝远,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曹锦炎等,成为新时期文字学、古文字学科研和教学的中坚力量。
21世纪以来,老成凋谢,青壮崛起,人才流动频繁,文字学研究中心和群体重新集结。以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裘锡圭、刘钊、陈剑为首的研究团队,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李学勤、赵平安、李守奎为首的研究团队,以吉林大学古籍所林沄、吴振武、冯胜君为首的研究团队,以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曾宪通、张振林、陈伟武为首的研究团队,以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王宁、李国英、李运富为首的研究团队,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李玲璞、臧克和、刘志基为首的研究团队,以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黄德宽、何琳仪、徐在国为首的研究团队,以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喻遂生、毛远明、张显成为首的研究团队,以首都师范大学甲骨文研究中心黄天树为首的研究团队,等等,都成为新的文字学研究基地和重镇,这些学科点为文字学研究的繁荣昌盛作出了应有贡献。
(二)、汉字研究的信息化与数字化
1.汉字编码
汉字编码是为汉字设计的一种便于输入计算机的代码,由于电子计算机现有的输入键盘与英文打字机键盘完全兼容,因而如何输入非拉丁字母的文字(包括汉字)便成了多年来人们研究的课题。汉字信息处理系统一般包括编码、输入、存储、编辑、输出和传输,编码是关键。不解决这个问题,汉字就不能进入计算机。
据粗略统计,现有400多种编码方案,其中上机通过试验的和已被采用作为输入方式的也有数十种之多。编码方案繁多,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1981年,国家标准局公布了《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简称汉字标准交换码),共分两级,一级3755个字,二级3008个字,共6763个字。这种汉字标准交换码是计算机的内部码,可以为各种输入输出设备的设计提供统一的标准,使各种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换有共同一致性,从而使信息资源的共享得以保证。
其中GB2312-80字符集,中文名国家标准字符集。收入汉字6763个,符号715个,总计7478个字符,这是大陆普遍使用的简体字字符集。GBK字符集,中文名国家标准扩展字符集,收入21003个汉字,882个符号,共计21885个字符,包括了中日韩(CJK)统一汉字20902个、扩展A集(CJK Ext-A)中的汉字52个。GB18030—2000字符集,包含GBK字符集和CJK Ext-A全部6582个汉字,共计27533个汉字。GB18030—2005字符集,在GB13030—2000的基础上,增加了CJK Ext-B的36862个汉字,以及其它的一些汉字,共计70244个汉字。方正超大字符集,包含GB18030—2000字符集、CJK Ext-B中的36862个汉字,共计64395个汉字。ISO/IEC 10646/Unicode字符集,这是全球可以共享的编码字符集,两者相互兼融,涵盖了世界上主要语文的字符,其中包括简繁体汉字,计有CJK统一汉字编码20992个、CJK Ext-A编码6582个、CJK Ext-B编码36862个、CJK Ext-C编码4160个、CJK Ext-D编码222个,共计68818个汉字。Ext-C还有2万多个汉字。
此外,对于古文字的计算机输入和输出,也有新的进展。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负责提供的甲骨文、《说文》小篆、金文和楚文字四个字表,形成提案文本提交IRG会议,已进入国际标准字符集的古文字编码单位。裘锡圭担任首席专家的“中华字库”工程,旨在建成全部汉字及少数民族文字的编码和主要字体字符集,形成汉字编码体系,研发汉字输入、输出、传播以及兼容等关键技术。
利用计算机处理汉字信息也是汉字学研究现代化的一个体现,有关研究可以参看陈爱文、陈朱鹤《汉字编码的理论与实践》(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冯志伟《现代汉字和计算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陈原《现代汉语用字信息分析》(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邢红兵《现代汉字特征分析与计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等论著。
2.古文字和出土文献数据库
从前整理古文字材料主要靠纸笔抄写、描摹、拓印等,效率低,效果差,利用不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照相和扫描技术的发展,彩照、红外线、高清扫描和图像处理等,使文字材料的面貌更真实,字形更清晰,从而为古文字材料的处理和传播提供了便利。
最能体现计算机技术效益的是各种数据库的建设和利用,不仅可以方便检索,提高研究效率,而且灵活性强,可以随时补充、调整。北京龙戴特信息技术公司与北京时代瀚堂科技公司联合开发的“龙语翰堂典籍数据库”是较有代表性的综合数据库,既有出土文献,也有传世文献。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开发的“中国基本古籍库”则主要是中国文化要籍的数字化,分为4个子库、20个大类和100个细目,共收录上自先秦下迄民国的历代名著和各学科基本文献10000余种。
专题性数据库也有不少。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牵头建设的“中国金石总录”数据库规模较大,整体规划共10期,现已完成8期,共收金石文献约30万种。另有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开发的“金文资料库”“金文字库”“战国楚简帛文字典型形体检索系统”,陕西考古研究所吴镇烽开发的“商周金文资料通鉴”,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制作的“中国古代简帛字形、辞例数据库”,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制作的“上博简字词全编资料库”“清华简字形辞例数据库”,安阳师院刘永革等开发的“甲骨文大数据云平台”等。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开发《说文解字》小篆字库,有效解决了现有小篆字库在调用小篆字体时出现乱码的问题。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小篆字库、德天甲骨文字库、华东师范大学“古文字电子资料库”等。刘志基等建设了“商周金文数字化处理系统”“战国楚文字数字化处理系统”,倡导通过输入单字中出现的偏旁进行检索,通过创建通用古文字偏旁数字平台,营造有助于偏旁分析法科学运用的数字化环境。
3. 古文字研究与人工智能
早在1977年,童恩正等就提出利用计算机缀合甲骨(童恩正、张陞楷、陈景春:《关于使用电子计算机缀合商代卜甲碎片的初步报告》,《考古》1977年第3期),近来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甲骨缀合取得成效,又有新的研究进展(王爱民等:《计算机辅助甲骨文缀合关键技术研究》,《计算机测量与控制》2010年第7期)。王爱民等成立“甲骨文计算机辅助”课题组,研究甲骨图像的轮廓信息的提取与轮廓跟踪算法、轮廓片段特征向量提取算法,建立甲骨文碎片数据库,并且研制基于边界匹配的甲骨文缀合辅助系统,让系统自动生成疑似目标甲骨碎片的动态数据库,并通过人机交互来实现甲骨文缀合。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利用人工智能识别古文字也提上了日程。2018年,吉林大学李春桃“人工智能识别古文字形体软件系统研发与建设”研究课题被列为“教育部、国家语委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与应用专项重大项目”,将在整理、释读先秦古文字资料的基础上,提取大量清晰的文字样本,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将其数字化、信息化,并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出一款古文字形体的自动识别软件。项目成果将会促进古文字专业的发展,加快古文字专业的普及化、大众化。
2019年5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发布AI+表意文字大数据成果——“文镜万象”出土文献智能识别释读系统之“商周金文智能镜”,开启了人类表意文字的学习、释读、研究智能化的全新方式。“商周金文智能镜”是对商周金文资料进行深度建设加工的数字化平台,运用人工智能领域多种前沿技术,首次实现商周金文多维度智能自动识别释读。它可以消除商周金文数字化现有的关键性盲点,通过字形识别来打通商周金文各类数据关联对接,盘活数字化营造的商周金文大数据系统,推动商周金文研究大踏步迈向智能化时代。
此外还有三维扫描和3D打印技术、笔迹甄别技术、DNA测定技术等,都被陆续运用到古文字材料的整理和研究中,整理古文字材料的科技手段大为改观。
(三)、文字学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1.世界文字学史与汉语文字学史
周有光介绍世界文字的发展史不遗余力。《字母的故事》《世界字母简史》《世界文字发展史》《人类文字浅说》等书贡献卓著。
汉字学史方面有刘又辛、方有国的《汉字发展史纲要》,曾宪通、林志强的《汉字源流》,黄德宽等的《古汉字发展论》,臧克和主编的《中国文字发展史》5卷本等。
20世纪90年代,黄德宽、陈秉新的《汉语文字学史》,孙钧锡的《中国汉字学史》,张其昀的《中国文字学史》,姚孝遂的《中国文字学史》陆续出版,内容角度各有侧重,学术评述互有不同。文字学史专题、专书、专人研究则为数更多。即使《说文》学也有张其昀的《“说文学”源流考略》、张标的《20世纪〈说文〉学流别考论》、党怀兴的《宋元明六书学研究》等综述性著作。
2.《说文》学研究的复兴
马叙伦的《说文解字六书疏证》运用所见的古文字材料对《说文解字》逐字进行了疏证。张舜徽的《说文解字约注》对《说文解字》作了简约说解。关于《说文解字》的通论性著作有陆宗达的《说文解字通论》,姚孝遂的《许慎与说文解字》。陆书从传统训诂以及现代语言学角度对《说文解字》作了系统介绍,姚书则大量运用古文字研究成果纠正了《说文解字》的错误。黄绮的《说文解字三索》探索许慎对形音义三方面说解的来源。其他如马宗霍的《说文解字引群书考》《说文解字引方言考》《说文解字引通人说考》,商承祚的《说文中之古文考》,蒋善国的《说文解字讲稿》等著作各有探讨。此外董希谦、张启焕的《许慎与说文解字研究》,余国庆的《说文学导论》,黄天树的《说文解字通论》对于《说文》进行了概论。石定果的《说文会意字研究》、李国英的《小篆形声字研究》分别对《说文解字》会意字、形声字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讨论。邹晓丽的《基础汉字形义释源——说文部首今读本义》,汤可敬的《说文解字今释》对于《说文解字》作了通俗新释。赵平安的《〈说文〉小篆研究》、蒋冀骋的《说文段注改篆评议》分别对《说文》篆书作了研究。
3.其他文字学史
自李运富的《楚国简帛文字构形系统研究》、王贵元的《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开始,王宁先生的弟子们一直致力于汉字构形史的研究。2003—2007年,王宁主编的《汉字构形史丛书》8册陆续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对于汉字构形史进行了全面梳理。
此外,陆锡兴的《汉字传播史》,董明的《古代汉语汉字对外传播史》,王锋的《从汉字到汉字系文字——汉字文化圈文字研究》对于汉字及其传播的历史作了全面回顾。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字学本体研究
一、古文字学的辉煌复兴
(一)古文字学的振兴
新中国成立后,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杨树达的《积微居金文说》,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容庚的《金文编》(第三版),容庚、张维持的《殷周青铜器通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甲骨文编》,于省吾的《甲骨文字释林》等重要成果陆续出版,为古文字学的振兴增添了动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文字学迎来发展高潮,出现许多通论性著作,如李学勤的《古文字学初阶》,林沄的《古文字研究简论》,高明的《中国古文字学通论》,陈炜湛、唐钰明的《古文字学纲要》,陈世辉、汤余惠的《古文字学概要》,何琳仪的《战国文字通论》,赵诚的《甲骨文字学纲要》,李圃的《甲骨文文字学》,刘钊的《古文字构形学》等。最新出版的有黄德宽的《古文字学》。此外,高明的《古文字类编》、徐中舒的《汉语古文字字形表》、李玲璞的《古文字诂林》、李学勤的《字源》、黄德宽的《古文字谱系疏证》、张亚初的《商周古文字源流疏证》等工具书也为古文字学的推广普及起到了促进作用。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后改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主编的《出土文献研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编的《出土文献》、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编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等集刊也为古文字学与出土文献研究的繁荣提供了出版保障。
值得关注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古文字学的名家宿儒从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等不同角度着手研究古文字学,都取得了突出成就,他们的论著结集成为业界学习和研究的经典样板和学术楷模。如《郭沫若全集·考古编》,《杨树达文集》,《于省吾著作集》,《唐兰全集》,《容庚学术著作全集》,《陈梦家著作集》,《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商承祚文集》,《张政烺文集》《张政烺文史论集》,《孙常叙古文字学论集》,《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于豪亮学术文存》,《李学勤集》《李学勤文集》《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李学勤卷》,《裘锡圭自选集》《裘锡圭学术文集》,《高明论著选集》《高明学术论集》,《林沄学术文集》《林沄学术文集(二)》,《曾宪通自选集》《曾宪通学术文集》,《姚孝遂古文字论集》,陈炜湛《三鉴斋甲骨文论集》《陈炜湛语言文字论集》,赵诚《古代文字音韵论文集》,刘雨《金文论集》,《马承源文博论集》,《陈佩芬青铜器论集》,李朝远《青铜器学步集》,杜廼松《古文字与青铜文明论集》《吉金文字与青铜文化论集》等,为后辈学习和借鉴提供了不同风格的学术范式和人门路径。
此外,中青年学者也步武前贤,续有发明。如李家浩《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丛书·李家浩卷》,何琳仪《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丛书·何琳仪卷》,李零《李零自选集》《万变:李零考古艺术史文集》《待兔轩文存》,黄天树《黄天树古文字论集》《黄天树甲骨金文论集》,黄锡全《古文字与古货币文集》,胡平生《胡平生简牍文物论集》《胡平生简牍文物论稿》,谢桂华《汉晋简牍论丛》,李均明《初学录》《耕耘录》《简牍法制论稿》,陈伟《燕说集》《新出楚简研读》,刘钊《古文字考释丛稿》《书馨集》《书馨集续编》,张懋镕《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一至五辑),王晖《古文字与中国早期文化论集》,冯时《古文字与古史新论》,张桂光《古文字论集》,赵平安《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续集》《金文释读与文明探索》《文字·文献·古史:赵平安自选集》,张玉金《古文字考释论集》,王蕴智《字学论集》,李守奎《汉字学论稿》《古文字与古史考——清华简整理研究》,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战国秦汉简帛丛考》,陈伟武《愈愚斋磨牙集》《愈愚斋磨牙二集》,徐在国《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丛书·徐在国卷》,陈剑《甲骨金文考释论集》《战国竹书论集》,白于蓝《拾遗录——出土文献研究》,董珊《简帛文献考释论丛》,陈英杰《文字与文献研究丛稿》,陈斯鹏《卓庐古文字学丛稿》,郭永秉《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续编》,范常喜《简帛探微》,谢明文《商周文字论集》等论集,其中有关研究也在古文字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新中国成立至今,古文字学科已经发展成为集甲骨学、金文学、战国文字学和简帛学等分支学科在内完善的学科体系。作为学科基础的古文字释读,在理论和方法上均有建树,许多疑难文字得到正确释读,完善了古老汉字的发展序列。在甲骨学领域,建立了甲骨文分类与断代研究的完整体系,为甲骨文字考释和殷商史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金文研究中,各诸侯国青铜器铭文的发现与研究,深化了人们对周代国家结构和地域文化的认知。战国文字分域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突破,揭示了战国时期各国语言文字的复杂性和交融性。简帛学研究发展迅速,前途远大,逐步形成文书研究和典籍研究两个新兴分支学科,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已经分道扬镳,各有侧重。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古文字学研究成就巨大,成果辉煌,值得大书特书。
下面我们分别具体论述。
(二)甲骨学研究
1.甲骨文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以甲骨文资料为例,郭沫若、胡厚宣《甲骨文合集》13册1978—1983年由中华书局陆续出齐。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小屯南地甲骨》,胡厚宣的《苏德美日所见甲骨集》《甲骨续存补编》,李学勤、齐文心、艾兰的《英国所藏甲骨集》《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藏甲骨文字》先后出版,加上后来彭邦炯等编著的《甲骨文合集补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曹玮的《周原甲骨文》等补充性的著录,以及种种新出土材料,为全面整理甲骨文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此外,焦智勤、段振美、党相魁等的《殷墟甲骨辑佚》,宋镇豪、焦智勤、孙亚冰的《殷墟甲骨拾遗》,濮茅左的《上海博物馆藏甲骨文字》,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甲骨卷》,李钟淑、葛英会的《北京大学珍藏甲骨文字》,宋镇豪、赵鹏、马季凡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甲骨集》,宋镇豪、玛丽娅的《俄罗斯国立爱米塔什博物馆藏殷墟甲骨》,宋镇豪、郭富纯的《旅顺博物馆所藏甲骨》,宋镇豪、黎小龙的《重庆三峡博物馆藏甲骨集》,葛亮的《复旦大学藏甲骨集》等甲骨文资料,也为学术界提供了更为清晰的拓本、照片和摹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胡厚宣、宋镇豪等主编的《甲骨文与殷商史》集刊也为甲骨学研究提供了发表平台。
在材料汇集的基础上,古文字学者还编纂了许多甲骨文工具书。如姚孝遂等的《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于省吾、姚孝遂等的《甲骨文字诂林》,何景成的《甲骨文字话林补编》,沈建华、曹锦炎的《甲骨文字形表》,曹锦炎、沈建华的《甲骨文校释总集》,李宗焜的《甲骨文字编》,刘钊等的《新甲骨文编》《甲骨文常用字字典》,徐中舒的《甲骨文字典》等等。综述性著作如王宇信的《甲骨学通论》,王宇信、杨升南的《甲骨学一百年》等等。
2.甲骨缀合
新中国成立后,专就抗战前发掘所获甲骨缀合的有郭若愚、曾毅公、李学勤的《殷虚文字缀合》。《甲骨文合集》充分吸收了学界已有的缀合成果,“总计拼合不下两千余版”,是一部集大成的甲骨缀合集,也为后续的甲骨缀合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把甲骨缀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近年来,由学苑出版社出版的黄天树的《甲骨拼合集》(一至五几集)又为甲骨缀合作出了新贡献。
3.甲骨断代
1951年起,陈梦家发表《甲骨断代学》(后收入《殷墟卜辞综述》),指出“文武丁卜辞”其实属于武丁时代,近年已得到考古发掘证据的支持。1977年,李学勤的《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文物》1977年第11期)提出了“历组卜辞”的概念,后在《小屯南地与甲骨分期》(《文物》1984年第5期)一文中,又提出殷墟甲骨分期两系说的概念,即一个系统是宾组——出组——何组——黄组,另一个系统是![]() 组——历组——无名组。裘锡圭的《论“历组卜辞”的时代》、(《古文字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林沄《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古文字研究》第9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予以支持并加以发展。黄天树的《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彭裕商的《殷墟甲骨断代》,李学勤、彭裕商的《殷墟甲骨分期研究》等专著均支持两系说,并有更具体的推阐和改进。“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们,利用先进的加速器质谱测定碳14方法技术测定甲骨的年代,也取得了新的重要成果。
组——历组——无名组。裘锡圭的《论“历组卜辞”的时代》、(《古文字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林沄《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古文字研究》第9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予以支持并加以发展。黄天树的《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彭裕商的《殷墟甲骨断代》,李学勤、彭裕商的《殷墟甲骨分期研究》等专著均支持两系说,并有更具体的推阐和改进。“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们,利用先进的加速器质谱测定碳14方法技术测定甲骨的年代,也取得了新的重要成果。
4.西周甲骨文
20世纪50年代以来,山西、陕西、北京等地陆续出土西周甲骨。至今已出土有字甲骨三百多片,总字数一千多个。其中最重要的一批,1977年出土于周原凤雏村甲组宫殿遗址内。西周甲骨的年代多为武成康时期,也有周文王和帝乙帝辛时期的。近年陕西岐山周公庙出土万余西周甲骨,又为西周甲骨研究补充了能源。
李学勤《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1期)一文,明确指出山西洪赵坊堆村所出有字甲骨“应当是西周的”,首次把西周甲骨与殷墟甲骨区别开来。研究西周甲骨的论著有王宇信的《西周甲骨探论》以及徐锡台的《周原甲骨文综述》等专著。
5.甲骨文字考释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甲骨文字考释取得了新的进展。如于省吾的《释从天从大从人的一些古文字》《释两》,张政烺的《释甲骨文俄、隶、蕴三字》《释它示——论卜辞中没有蚕神》《殷墟苜字说》,李学勤的《释郊》,裘锡圭的《释柲》《甲骨文字考释(八篇)》《释![]() 》《释殷墟甲骨文里的“远”“
》《释殷墟甲骨文里的“远”“![]() ”(迩)及有关诸字》《甲骨文中的见与视》,林沄的《说飘风》等文,均有创获。
”(迩)及有关诸字》《甲骨文中的见与视》,林沄的《说飘风》等文,均有创获。
(三)金文与青铜器研究
1.金文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金文资料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殷周金文集成》共18册,由中华书局于1994年完成出版。此后刘雨、卢岩的《近出殷周金文集录》,刘雨、严志斌的《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等对新见青铜器续作了增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殷周金文集成释文》,并18册为6卷,已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最新者为吴镇烽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张桂光、秦晓华的《商周金文摹释总集》为商周金文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摹本。索引如张亚初的《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的《金文引得(殷商西周卷)》《金文引得(春秋战国卷)》,张桂光的《商周金文辞类纂》。金文字典方面,有容庚的《金文编(第四版)》,陈汉平的《〈金文编〉订补》,董莲池的《〈金文编〉校补》《新金文编》,陈斯鹏等的《新见金文字编》,严志斌的《四版金文编校补》《商金文编》,张俊成的《西周金文字编》,陈初生的《金文常用字典》,戴家祥的《金文大字典》,张世超的《金文形义通解》等等。通论、通释性著作如马承源的《中国古代青铜器》《中国青铜器》《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杜迺松的《中国青铜器发展史》,朱凤瀚的《古代中国青铜器》《中国青铜器综论》,陈佩芬的《夏商周青铜器研究》,张懋镕的《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唐兰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董莲池的《商周金文辞汇释》等等。
2.金文分期
在郭沫若“标准器断代法”的研究基础上,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唐兰的《西周铜器中的“康宫”问题》《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西周铜器铭文分代史征》等论著,在青铜器的分期断代研究上又续有推进。一些学者还进一步结合地层关系,利用墓葬和窖藏青铜器,选择具有标尺作用的铜器群,通过同群和异群各器间的关系来进行商周青铜器分期断代。郭宝钧的《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李学勤的《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周原庄白、强村两处青铜器窖藏的综合研究》,刘启益的《微氏家族铜器与西周铜器断代》都是这一时期青铜器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也向多学科交叉综合发展。其中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的《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一书体现了新时期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的最新进展。
3.金文分域
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有论著将各种战国文字材料集中起来,依《说文》“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之说,划分为三晋、燕、齐、楚、秦五系,给这个学科分支的建立开拓了道路。80年代以后,金文分域的研究又有新的进展。吴镇烽的《陕西金文汇编》,黄锡全的《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山东省博物馆的《山东金文集成》,孙合肥的《安徽商周金文汇编》,张天恩的《陕西金文集成》等对于各地所出青铜器铭文作了集录。
由于新材料不断发现,青铜器分域甚至分国研究得到飞跃发展。楚国青铜器如李零的《楚国铜器铭文编年汇释》《论东周时期的楚国典型铜器群》,刘彬徽的《楚系青铜器研究》,刘彬徽、刘长武的《楚系金文汇编》,邹芙都的《楚系铭文综合研究》,对楚系青铜器及其铭文作了全面收集整理和研究。即使安徽出土青铜器,也有崔恒昇的《安徽出土金文订补》,程鹏万的《安徽寿县朱家集出土青铜器铭文集释》,陈治军的《安徽出土青铜器铭文研究》等研究。甚至同为楚系的曾国青铜器也已有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曾国青铜器》辑录研究。
吴越等国青铜器及其铭文也有不少学者辑录研究。董楚平的《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曹锦炎的《吴越青铜器铭文述编》,施谢捷的《吴越文字汇编》,对两周时期吴越徐舒的铜器铭文进行了汇释研究。
1971年河南新郑发现韩国青铜兵器200多件,上面的铭文是研究三晋文字的极好材料。黄盛璋的《三晋铜器的国别、年代与相关制度》《试论三晋兵器的国别和年代及其相关问题》等卓有贡献。1977年,河北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王墓出土青铜大鼎、方壶、圆壶铭文,也促进了战国文字研究。张守中的《中山王![]() 器文字编》汇集了中山王
器文字编》汇集了中山王![]() 墓出土的文字资料。
墓出土的文字资料。
黄盛璋的《战国燕国铜器铭刻新考》等全面考察了燕国青铜器。王辉的《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秦出土文献编年》《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等,也对秦青铜器铭文等作了集录。
4.金文考释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具体的金文文字考释上有突出贡献的学者很多,如张政烺的释“![]() ”》,林沄的《说王》《豐、豊辨》,高明的《䀇、簠考辨》,于豪亮的《说引字》《说俎字》,曾宪通的《说繇》,马承源的《说
”》,林沄的《说王》《豐、豊辨》,高明的《䀇、簠考辨》,于豪亮的《说引字》《说俎字》,曾宪通的《说繇》,马承源的《说![]() 》等许多论文,都在金文文字的考释上提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见解。裘锡圭、李学勤等都在金文文字考释上取得了突出成就。如裘锡圭的《史墙盘铭解释》《畀字补释》《说
》等许多论文,都在金文文字的考释上提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见解。裘锡圭、李学勤等都在金文文字考释上取得了突出成就。如裘锡圭的《史墙盘铭解释》《畀字补释》《说![]() 簋的两个地名——“棫林”和“胡”》《西周铜器铭文中的“履”》《释建》《说金文“引”字的虚词用法》等文,都能考察字形,严密论证,故能精审可信。与李家浩合作的《谈曾侯乙墓钟磬铭文中的几个字》释“
簋的两个地名——“棫林”和“胡”》《西周铜器铭文中的“履”》《释建》《说金文“引”字的虚词用法》等文,都能考察字形,严密论证,故能精审可信。与李家浩合作的《谈曾侯乙墓钟磬铭文中的几个字》释“![]() ”为“申”,彻底平息了多年来关于安徽寿县“蔡侯
”为“申”,彻底平息了多年来关于安徽寿县“蔡侯![]() ”青铜器组年代问题的纷争。
”青铜器组年代问题的纷争。
此外,李学勤的《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释“贾”,《试论孤竹》释“孤竹”,《多友鼎的“卒”字及其他》释“卒”,《由沂水新出盂铭释金文“总”字》释“总”,《枣庄徐楼村宋公鼎与费国》释“![]() ”为“固”等,也无不发人所未发。
”为“固”等,也无不发人所未发。
一些后起之秀对金文考释也颇多发明,如陈剑的《柞伯簋铭补释》释“贤”,《西周金文“牙僰”小考》释“牙僰”为“邪幅”,堪称允当。
(四)战国文字研究
1.战国文字研究概述
20世纪古文字考释成就突出表现在战国文字的释读水平的显著提高,尤其是张政烺、饶宗颐、朱德煕、李学勤、裘锡圭、黄盛璋、曾宪通、李家浩、吴振武、何琳仪、李零等学者,一直致力于战国文字研究。
战国文字研究包含甚广,诸如金石、简帛、货币、玺印、陶文等文字载体,资料琐碎,搜集不易。而且与其他学科多有交叉,以往一向视为学术难点。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出土,战国文字资料积累日益丰富,使战国文字释读水平迅速提高。朱德熙的《寿县出土楚器铭文研究》《洛阳金村出土方壶之校量》《战国记容铜器刻辞考释四篇》等论文,对战国文字考释创获甚多。李学勤的《战国题铭概述》一文,系统收集整理战国文字,注重分域断代和释读,第一次提出了“五系说”,在战国文字研究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楚文字研究进步明显。1950年代寿县发掘蔡侯墓时所得器铭及寿县发现的鄂君启节铭文,经郭沫若、于省吾、黄盛璋、朱德熙、李家浩等先后深入研究,创获甚大。20世纪70年代末在湖北随县发掘所得的曾侯乙墓编钟编磬铭文,裘锡圭的《谈谈随县曾侯乙墓的文字资料》,裘锡圭、李家浩的《曾侯乙墓钟磐铭文说明》以及饶宗颐、曾宪通的《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曾宪通的《关于曾侯乙编钟铭文的释读问题》等论著作了很好的探讨,是文字考释方面比较重要成果。
20世纪70年代以后其他系文字的释读研究也有显著提高。1977年河北平山所出的“中山三器”的考释,短短数年,便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张政烺的《中山王![]() 壶及鼎铭考释》《中山国胤嗣
壶及鼎铭考释》《中山国胤嗣![]()
![]() 壶释文》,朱德熙、裘锡圭的《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铭文的初步研究》,李学勤、李零的《平山三器与中山国史的若干问题》,于豪亮的《中山三器铭文考释》等皆属名篇。
壶释文》,朱德熙、裘锡圭的《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铭文的初步研究》,李学勤、李零的《平山三器与中山国史的若干问题》,于豪亮的《中山三器铭文考释》等皆属名篇。
2.战国文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战国文字研究突破的另一个标志是各系区域文字的汇集编纂。袁仲一《秦文字类编》、王辉《秦文字编》、刘孝霞《秦文字编》,李守奎《楚文字编》,汤志彪《三晋文字编》、张道升《侯马盟书文字编》,孙刚《齐文字编》、张振谦《齐鲁文字编》,施谢捷《吴越文字汇编》等,分别对秦系、楚系、晋系、齐系、吴越等地的文字作了编辑汇总。
其他战国文字资料汇编也有新的突破,如汪庆正《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卷》,朱活《中国钱币大辞典·先秦编》,张颔《古币文编》,商承祚、王贵忱、谭棣华《先秦货币文编》,吴良宝《先秦货币文字编》,罗福颐《古玺汇编》《古玺文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邱传亮《楚官玺集释》,文雅堂《秦官印封泥聚》,许雄志《秦印文字汇编》《鉴印山房藏古封泥菁华》,孙慰祖《古封泥集成》,傅嘉仪《秦封泥汇考》《新出土秦代封泥印集》《历代印陶封泥印风》,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路东之《古陶文明博物馆藏封泥集》,杨广泰《新出封泥汇编》,任红雨《中国封泥大系》,高明、葛英会、涂白奎《古陶文汇编》《古陶文字征》《古陶字录》,王延林、徐谷甫《古陶字汇》,王恩田《陶文图录》《陶文字典》,徐在国《新出古陶文图录》《新出齐陶文图录》,袁仲一《秦代陶文》,罗福颐《石刻篆文编》,徐宝贵《石鼓文整理研究》等等,涵盖了战国货币、玺印、封泥、陶文、石刻等众多文字资料。
3.战国文字考释
20世纪70年代以来,朱德熙、裘锡圭《战国文字研究》(六种)《信阳楚简考释》(五篇)《战国铜器铭文中的食官》,朱德熙《战国陶文和玺印文字中的“者”字》《战国文字中所见有关厩的资料》,裘锡圭《战国货币考》(十二篇)《战国文字中的“市”》《战国玺印文字考释》(三篇)等合作或分别撰写了一系列战国文字的研究和考释文章,使战国文字的释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他们这一时期的古文字研究成果主要结集于《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以及裘锡圭《古文字论集》二书中。此外如李家浩《释弁》《信阳楚简“浍”及从“龹”之字》《战国货币文字中的“㡀”和“比”》《战国时代的“冢”字》,吴振武《战国货币铭文中的“刀”》《释“受”并论盱眙南窑铜壶和重金方壶的国别》,黄盛璋《战国“冶”字结构类型与分国研究》等研究文章对战国金文中的一些疑难字作出了正确的考释。李零《战国鸟书箴铭带钩考释》一文,对带钩及其他战国金文中的所见的相关疑难文字作出了正确的考释,也是鸟书研究的重要论著。如此种种,均称得上战国金文考释中的重要收获。
战国文字研究在改革开放以后进步非常快。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一书,对战国金文及其他文字作了更详尽细致、全面系统的梳理,代表了20世纪该领域阶段性综合研究的水平。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汤余惠《战国文字编》的出版,可以作为这个学科分支成熟的标志。王辉、陈昭容、王伟《秦文字通论》则对于秦文字作了系统总结。
(五)简帛文字研究
1.简帛文字研究概述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简帛的发现连续不断,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有许多重大的发现,如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简,1973年长沙马王堆帛书,1974年新居延汉简,1975年云梦睡虎地秦简,1983年江陵张家山汉简,1992年敦煌悬泉置汉简,1993年荆门郭店楚简,1994年上海博物馆藏楚简,1996年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2002年龙山里耶秦简,2007年岳麓书院藏秦简,2008年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2009年北京大学藏秦汉简等。对这些新发现的简帛,有众多学者进行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国家文物局出土文献整理小组(后成为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的成立是一个重要的契机。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编的《简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简帛研究中心主编的《简帛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甘肃简牍博物馆联合主办的《简牍学研究》,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张显成编辑的《简帛语言文字研究》等刊物和网站也已取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由于简帛的内容有书籍与文书之分,研究的方法和途径彼此不同,近年来简帛学又有进一步细化的趋势,恐怕不久就会成为两个分支了,尤其是简帛古书的出土,有些可与传世文献对照,使得大规模释字成为可能。
2.简帛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简帛资料更为大宗,只能分时、分系进行概述。如战国楚系简帛方面有:李零《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研究》,商承祚《战国楚竹简汇编》,湖北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望山楚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九店楚简》,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陈松长《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九)》,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捌)》,等等。
秦系简帛方面有: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国文物研究所等《龙岗秦简》《关沮秦汉墓简牍》,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放马滩秦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简(壹)、(贰)》,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伍)》,等等。
汉代简帛方面有: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威汉简》,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县文化馆《武威汉代医简》,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叁)(肆)》,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贰)》,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一)—(五)》,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乙编》,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肩水金关汉简(壹)—(伍)》,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简—甲渠侯关与第四燧》,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居延新简—甲渠侯关》,魏坚《额济纳汉简》,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研究》,韩自强《阜阳汉简〈周易〉研究》,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湖北省考古研究所《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关沮秦汉墓简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连云港市博物馆等《尹湾汉墓简牍》,等等。
三国吴简方面有:《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捌)》,等等。
简帛文字整理与研究的集大成者体现为有关工具书的编纂方面。秦简方面如张世超、张玉春《秦简文字编》,方勇《秦简牍文编》,陈振裕、刘信芳《睡虎地秦简文字编》,张守中《睡虎地秦简文字编》、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叁)文字编》,蒋男《里耶秦简文字编》,张显成《秦简逐字索引》等。楚系简帛方面如郭若愚《战国楚简文字编》,葛英会、彭浩《楚国简帛文字编》,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蔡丽利《楚卜筮简文字编》,曾宪通《长沙楚帛书文字编》,张光裕、黄锡全、滕壬生《曾侯乙墓竹简文字编》,张守中《包山楚简文字编》《郭店楚简文字编》,程燕《望山楚简文字编》,张新俊、张胜波《新蔡葛陵楚简文字编》,李守奎《楚文字编》,李守奎、贾连翔、马楠《包山楚墓文字全编》,李守奎、曲冰、孙伟龙《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五)文字编》,李学勤、沈建华、贾连翔《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文字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陆)文字编》,徐在国《楚帛书诂林》,张显成《楚简帛逐字索引》等。汉代简帛方面如骈宇骞《银雀山汉简文字编》,陈松长《马王堆简帛文字编》,张守中《张家山汉简文字编》,陆锡兴《汉代简牍草字编》,陈建贡、徐敏《简牍帛书字典》等等。
以上这些大宗的简帛文字资料整理与研究,极大地提升了简帛文字的研究水平。
3.简帛文字考释与研究
简帛文字是最早的手书文字,异体众多,辨识不易,很多学者的文字学考释也常常聚焦于此,可谓成果丰硕,汗牛充栋,各种语言文字的论著已达数千种。即以简帛语言文字研究为例,各种释文、注释、索引、文字编等等,已经不计其数。由于篇幅所限,一时难以赘述,只能简单概述一些宏观性、综合性和普遍性的研究。
除了汉晋简帛文字以外,先秦简帛文字以秦系和楚系为主。在秦系简帛文字中,以“古隶”的发现尤为重要。裘锡圭《从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谈关于古隶的一些问题》、吴白匋《从出土秦简帛书看秦汉早期隶书》、曾宪通《秦至汉初简帛篆隶的整理和研究》、赵平安《隶变研究》、任平《说隶》等论著对于秦汉早期隶书的发展演变作了新的探索。
在楚系简帛文字中,马国权《战国楚竹简文字略说》,黄锡全《楚系文字略论》,罗运环《论楚文字的演变规律》,李守奎《楚文字研究与“楚文字学”的构建》《楚文字的历史发展与地域文字系统的形成》等文,力图从宏观和综合的角度概括楚文字研究与“楚文字学”的发展演变。
此外,于豪亮《释汉简中的“草书”》、裘锡圭《谈谈辨释汉简文字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谢桂华《汉简草书辨正举隅》等文对于辨识汉简中的“草书”等贡献颇著。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些非常重要的古文字学成果就是在简帛文字的启发下获得的。比如,于豪亮受云梦睡虎地秦简、长沙马王堆帛书“引”字的启发释出了甲骨文、金文中的“引”字,(于豪亮:《说引字》,《考古》1977年5期)裘锡圭据云梦睡虎地秦简中的“![]() ”字释出甲骨文中的“
”字释出甲骨文中的“![]() (害)”字。(裘锡圭:《释“
(害)”字。(裘锡圭:《释“![]() ”》,香港中文大学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究会《古文字学论集(初编)》,1983年)而从古文字学角度来说,楚简文字直接就是战国文字中的楚系文字,它们的某些字形变化多端,有时看似诡异,其实还保留着更古老的源源,甚至可以上溯到商代甲骨文和西周金文。
”》,香港中文大学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究会《古文字学论集(初编)》,1983年)而从古文字学角度来说,楚简文字直接就是战国文字中的楚系文字,它们的某些字形变化多端,有时看似诡异,其实还保留着更古老的源源,甚至可以上溯到商代甲骨文和西周金文。
李学勤先生以郭店楚简为例指出,“前人考释商周文字,由《说文》出发,但是《说文》主要是小篆,所录古籀无多,而秦汉小篆上距西周春秋文字差了一大截,更不要说殷商了。战国文字上承春秋,下启秦汉,列国异形,又多变化,极其需要研究。郭店简发表后,利用简中文字的研究成果,进而考定商或西周文字,已有一些成功例子,值得接着做下去”(张守中等:《郭店楚简文字编》李学勤序,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比如郭店楚简《老子》丙组“视之不足见”等“视”、“见”同见于一简而字形微有不同,裘锡圭从中悟出甲骨文中亦有类似区别。(裘锡圭:《甲骨文中的“见”与“视”),《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陈剑据郭店楚简《唐虞之道》“贤”字释出西周金文《柞伯簋》“贤获”,并与《仪礼》等有关礼制联系起来,(陈剑:《柞伯簋铭补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9年1期。按随县楚简中也有“贤”字,何琳仪:《随县竹简选释》(《华学》第七辑)以为即地名“宛”)可谓一大创见。又如楚文字中常见的“![]() (就)”字,以前虽然经过很多学者考释,众说纷纭,但是只有在楚简出土之后才完全破解,原来它与甲骨文、金文的“
(就)”字,以前虽然经过很多学者考释,众说纷纭,但是只有在楚简出土之后才完全破解,原来它与甲骨文、金文的“![]() ”字一脉相承。(朱德熙:《释
”字一脉相承。(朱德熙:《释![]() 》,《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2页;李零:《古文字杂识(两篇)》,《于省吾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又《郭店楚墓竹简》第189页注释[一])再如李家浩在郭店楚简《六德》等“昆弟”辞例的基础上才考释出楚简文字中的古文“昆”字,并分析其造字本义是“昆虫之‘昆’的象形”。(李家浩:《楚墓竹简中的“昆”字及从“昆”之字》,《中国文字》新25期,[台湾]艺文印书馆1999年版;又《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第30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郭店楚墓竹简》第189页注释[一七]裘锡圭先生按语云:“‘弟’上一字不识(《尊德义》篇有以之为声旁的从心之字),但可知其必当读为‘昆弟’之“昆’。”实际上已经释出了“昆”字,只是没有进行字形分析罢了。)类似之例颇多,此不赘举。
》,《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2页;李零:《古文字杂识(两篇)》,《于省吾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又《郭店楚墓竹简》第189页注释[一])再如李家浩在郭店楚简《六德》等“昆弟”辞例的基础上才考释出楚简文字中的古文“昆”字,并分析其造字本义是“昆虫之‘昆’的象形”。(李家浩:《楚墓竹简中的“昆”字及从“昆”之字》,《中国文字》新25期,[台湾]艺文印书馆1999年版;又《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第30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郭店楚墓竹简》第189页注释[一七]裘锡圭先生按语云:“‘弟’上一字不识(《尊德义》篇有以之为声旁的从心之字),但可知其必当读为‘昆弟’之“昆’。”实际上已经释出了“昆”字,只是没有进行字形分析罢了。)类似之例颇多,此不赘举。
其实简帛文字对于古文字考释启示更多的还在于方法论方面。简帛文字的优势就是文字多,篇幅长,无论是字形分析还是辞例推勘都有极大的发挥余地。但简帛文字最独特的一点就是很多简帛文献可以与传世文献对读,这又为简帛文字的考释添一新途径。由于简帛文字特有的优长,有学者形容古文字研究已经进入“大规模识字阶段”,甚至有学者认为“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这三个名词,串起了近二十年来的汉语古文字学,特别是战国文字研究的主脉”。(郭水秉:《字认完了吗?》,《文汇报》2015年5月29日第7版)
目前的楚系简帛文字考释,除了古文字学方法以外,或采取文献学对读方法,尽量为出土本找出今本的根据和来源,把古文字某字直接对应于今本某字,可以按图索骥,唾手可得。不足之处是这些字的形音义等,我们有时还弄不清楚。如古文字“![]() ”字多见,在郭店楚简《老子》《缁衣》出土后,经与今本对照,始知是“失”字。(《郭店楚墓竹简》,第114页注释[二八])至于字形结构分析,李家浩释为“迭”(《读〈郭店楚墓竹简〉琐议》,《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赵平安释为“逸”(《战国文字的“
”字多见,在郭店楚简《老子》《缁衣》出土后,经与今本对照,始知是“失”字。(《郭店楚墓竹简》,第114页注释[二八])至于字形结构分析,李家浩释为“迭”(《读〈郭店楚墓竹简〉琐议》,《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赵平安释为“逸”(《战国文字的“![]() ”与甲骨文“
”与甲骨文“![]() ”为一字说》,《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二辑,中华书局2000年版),究属何字,尚待研究。又如楚简中的“
”为一字说》,《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二辑,中华书局2000年版),究属何字,尚待研究。又如楚简中的“![]() (一)”字(《郭店楚墓竹简》第126页注释[一一]、第152页注释[一七],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等,虽然经过很多学者考释,众说纷纭,但是只有在楚简出土之后才完全破解。但是我们虽然知道其用法,其造字本义、所从声符等仍不了解。这说明“
(一)”字(《郭店楚墓竹简》第126页注释[一一]、第152页注释[一七],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等,虽然经过很多学者考释,众说纷纭,但是只有在楚简出土之后才完全破解。但是我们虽然知道其用法,其造字本义、所从声符等仍不了解。这说明“![]() (一)”字等古文字学的考释虽然已经完结,但是文字学的考释依然任重道远。
(一)”字等古文字学的考释虽然已经完结,但是文字学的考释依然任重道远。
二、近代汉字学与现代汉字学的发展壮大
(一)近代汉字学的发展
1. 近代汉字学的成立
与“古文字学”对应,唐兰提出了“近代文字学”的学科分支概念。经朱德熙、李荣、蒋礼鸿、郭在贻、张涌泉、杨宝忠等倡导,目前已成为汉字学研究的重要部分。2007年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发布的“文字学名词”中把“近代汉字”定义为“秦汉以后至20世纪初叶使用的以隶书和楷书为主体的汉字书写符号系统”。
近代汉字学理论方面的探讨有蒋礼鸿的《中国俗文字学研究导言》(《杭州大学学报》1959年第3期)对俗字研究的现状和意义、俗字研究的步骤和方法等作了独到的分析和阐述,指明了俗文字学的研究方向。许长安的《近代汉字学刍议》、张鸿魁的《近代汉字研究的几个问题》、刘金荣的《“近代汉字”刍议》、梁春胜的《“近代汉字学”刍议》等文也对近代汉字学的概念作了辨析。
2. 近代汉字学研究
“俗字”研究是近代文字学中学科分支的重心。施安昌的《唐代正字学考》,陈五云的《俗文字学刍议》,郭在贻、张涌泉的《俗字研究与古籍整理》,张涌泉的《敦煌写卷俗字的类型及其考辨方法》等文对于俗字研究的重要性进行了阐发。特别是李荣的《文字问题》和张涌泉的《汉语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陈五云的《从新视角看汉字:俗文字学》等专著,标志着俗字研究有了质的飞跃,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张涌泉的《汉语俗字丛考》是其俗字考释的集大成之作。
郭沫若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提出《兰亭序》真伪问题之后,魏晋时代楷书、行书的真面貌这个老问题,又引起一些讨论。有关学术争鸣已经结集在《兰亭论辨》一书中。启功的《古代字体论稿》对先秦以下各种字体作了全面研究。汉语大字典字形组编的《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收入了一些秦汉魏晋时期的文字字形。
汉代以后的文字材料非常丰富,碑刻文字是研究重点。有关论著如:罗振鋆、罗振玉《增订碑别字》,秦公《碑别字新编》,秦公、刘大新《碑别字新编(修订本)》《广碑别字》,马向欣《六朝别字记新编》等。欧昌俊、李海霞《六朝唐五代石刻俗字研究》,曾良《隋唐出土墓志文字研究及整理》,陆明君《魏晋南北朝碑别字研究》,郭瑞《魏晋南北朝石刻文字》,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研究》《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典》《西南大学新藏墓志集释》,张颖慧《魏晋南北朝石刻文字整理与研究》,何林英《两汉碑刻隶书字体研究》,杨宏《北魏石刻楷书构形系统研究》等专著各有发明。毛远明《碑刻文献学通论》,曾晓梅《碑刻文献论著叙录》是对于学科的回顾总结。
纸质手写文本也是近代汉字的重要材料,包括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献等。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敦煌写本文献学》、曾良《敦煌文献字义通释》、蒋冀骋《敦煌文献研究》、黄征《敦煌俗字典》等成果是关于敦煌俗字方面的。
疑难俗字的考释是近代汉字研究的热点。杨宝忠先后出版的《疑难字考释与研究》《疑难字续考》《疑难字三考(上下)》,对《汉语大字典》等大型字书中的数千个音义未详或辨析有误的疑难俗字进行系统梳理考证。对于其他文书及古籍俗字有方孝坤的《徽州文书俗字研究》,温振兴的《影戏俗字研究》,曾良的《俗字及古籍文字通例研究》《明清小说俗字研究》,周志锋的《明清小说俗字俗语研究》等专著。
(二)现代汉字学
现代汉字通常指20世纪以后的汉字。周有光的《现代汉字学发凡》(《语文现代化》(丛刊)第2辑,1980年)提出“现代汉字学”的学术定位,之后通论性的论著有孙钧锡的《汉字通论》,张静贤的《现代汉字教程》,高家莺、范可育、费锦昌的《现代汉字学》,苏培成的《现代汉字学纲要》,杨润陆的《现代汉字学通论》,高更生的《汉字研究》,潘钧《现代汉字问题研究》等专著。
汉字改革,包括汉字简化和规范,是现代汉字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方面论著很多。如易熙吾的《简体字原》、陈光尧的《简化汉字字体说明》等,侧重各不相同。改革开放以来发表的主要有陈永舜的《汉字改革史纲》,郑琳曦的《汉字改革》,武占坤、马国凡的《汉字·汉字改革史》,孙钧锡的《汉字和汉字规范化》,尹斌庸,John. S. Rohsenow的《现代汉字》(英文版),张书岩等的 《简化字溯源》《异体字研究》,厉兵的《汉字字形研究》,傅永和的《规范汉字》,李宇明的《汉字规范》《汉字规范百家谈》等专著,对于新时期的汉字简化和汉字规范作了学术探讨。
三、比较文字学与应用文字学的蓬勃开展
(一)比较文字学的开展
20世纪90年代,王元鹿的《比较文字学》,周有光的《比较文字学初探》先后问世。随着这门学科的不断成长,“比较文字学”也逐渐为人们所熟悉。之前王元鹿的《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比较研究》反映了汉古文字和东巴文字同属意音文字的共性,更揭示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两种文字的独特个性和风格差异,无疑非常有助于比较文字学学科理论的建立及文字发展史和普通文字学理论研究。
喻遂生及其学生一直致力于古汉字与纳西东巴文的比较研究,如喻遂生《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第二辑)》等著作即其成果体现。
拱玉书等的《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一书分别对这三种古文字的起源及结构类型作了比较分析。通过对三种文字起源传说及考古实物等多种材料的研究,认为早期文字都是象形字及象形字的派生字。认为甲骨文和原始楔形文字作为文字体系,在用字上都以表义为主,表音为辅,古埃及文字则以表音为主。此外,黄亚平及其学生则致力于古汉字与古埃及圣书字、苏美尔原始楔形文字、玛雅文象形字的比较研究,也取得了很多成果。
(二)应用文字学的壮大
1. 异体字整理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也作过搜集工作。具体成果有《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汉语大字典·异体字表》,戴召萃的《异体字字典》,李圃的《汉字异体字大字典》等。《中国异体字大系》分为“篆书编”“楷书编”“隶书编”,也由上海书画出版社陆续付梓。
2. 字典编纂
编纂字典的水平是文字研究水平的反映。如《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这些规模各异的字典、词典都广泛发行,广受好评。张双棣、陈涛的《古代汉语字典》、王力的《王力古汉语字典》是较好的中型字典。收字最多的则是冷玉龙、韦一心的《中华字海》。
3. 汉字学知识的普及和应用
汉字的教学与研究对文字学的迅猛发展起到了互动作用。在汉字教学中,高等教育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中一般都会按照学科要求设置文字学课程,讲授一些汉字学的基础知识;个别高校还会开设古文字学(甚至分支学科)或者俗字学等专门课程,教育和培养有关人才。教学相长,本文前面提到的不少文字学专著其实也是大学授课的指定教材,“六书说”“三书说”甚至“二书说”等各有市场,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可以说高校和科研院所是文字学研究的骨干力量。
文字学的迅猛发展对于汉字的普及和应用起到了推动作用。一些学者也撰写了不少古文字普及著作,如左民安的《汉字例话》《汉字例话续编》,李乐毅的《汉字演变五百例》,陈炜湛的《古文字趣谈》《汉字古今谈》《汉字古今谈续编》,等等。谷衍奎的《汉字源流字典》等工具书的出版对普通读者了解古今汉字的发展源流有一定贡献。
《说文》学方面也有学者作了一些普及工作。张舜徽的《说文解字导读》、王梦华的《说文解字释要》、苏宝荣的《说文解字助读》,王宁、董希谦主编的《许慎与〈说文〉小丛书》,这些书对《说文解字》知识的普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外如夏渌《评康殷文字学》也对一些似是而非的流行说法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同时,对于社会正确使用规范汉字,新闻出版和媒体也配合作了不少工作和宣传。1995年创刊的《咬文嚼字》是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发行的文艺月刊,以“宣传语文规范,传播语文知识,引导语文生活,推动语文学习”为办刊宗旨,纠正了媒体艺人、名家作品中的不少错别字。诸如中央电视台“汉字听写大会”、河南电视台“汉字英雄”、浙江电视台“汉字风云会”、湖南电视台“神奇的汉字”等,对于汉字知识的普及和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同时,一些与国家语文政策不符的现象也值得警惕,如繁简混用等社会用字混乱现象屡见不鲜。受境外影响,甚至出现把“繁体字”称为“正体字”的倾向,社会上有不少非专业人士呼吁恢复繁体字,个别中小学教育中也出现了一些“识繁用简”的试点工作。“繁体字”的回流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
在文字学应用理论方面,万业馨的《应用汉字学概要》对于应用汉字学作了概述。齐冲天的《书法文字学》,马鹏程的《汉字笔迹心理学——笔迹心理分析技术与应用》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汉字书写在书法和笔迹鉴定上的应用。
四、文字学研究70年以来的经验教训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文字学研究,走过了一个极不平凡的光辉历程。尤其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研究视野更为宽广,研究领域更为壮大,研究方法更为多元,跨学科和跨领域的学术交叉更为常见。传统古文字“绝学”不但不绝,而且随着时代发展,还增设了很多新兴和交叉学科。其中尤以出土文献和古文字研究发展迅速,是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典型,近些年来已经独立出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简帛文字研究等四大分支学科,取得了世界领先的学术地位。而近代文字学和现代文字学的蓬勃兴起,也与建国后汉字简化的改革潮流一脉相承,同样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尽管如此,辉煌背后亦有隐忧,文字学研究仍然存在某些研究短板和薄弱环节。除了汉字学研究国际领先以外,国内的普通文字学研究与世界水平相距甚远,比较文字学研究也差强人意,只能就境内外一些常见文字进行常规比较,缺乏细致深入的学术探讨。不少研究者重实践而轻理论,热衷于具体的文字考释,对于文字学理论不感兴趣。即使是文字学理论,也相对缺乏广阔的学术视野,最终沦为单纯的汉字学研究。
回顾70年以来的文字学研究,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同样珍贵。学术研究与政治社会的互动,并不总是正相关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字学研究受到严重干扰,出现长期停滞的局面。改革开放以来,汉字学研究不断突破原有的理论禁区,逐步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极力从汉字的实际出发,去探索汉字发展和演变的普遍规律。近些年来,由于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以及评价机制的影响,一些研究者过分追逐学术热点,对于新发现趋之若鹜,浅尝辄止;而对于学术研究的“硬骨头”则避之不及,无暇问津。只求“短平快”一时的经济效益,缺乏“十年磨一剑”的沉潜和耐心,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影响到了文字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值得学界警醒。
总结历史,展望未来,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文字学研究既是一个历史高峰,也是一个崭新起点,为文字学研究迈上更高台阶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抚今追昔,继往开来,只有吸取70年以来文字学研究的经验教训,惩前毖后,扬长补短,才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取得更为伟大的学术成就。
参考文献:
冯时:《中国古文字学研究五十年》,《考古》1999年第9期。
黄德宽、陈秉新:《汉语文字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李行健、余志鸿:《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语言学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李学勤:《从“绝学”到“显学”——中国古文字学的繁荣发展》,《人民日报》2009年8月14日。
李学勤:《建国六十年来甲骨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殷都学刊》2010年第1期。
李运富、温敏、韦良玉:《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文字学研究》,《孔学堂》2018年第3期。
刘源:《新世纪甲骨学的快速发展》,《中国史研究动态》2015年第4期。
罗卫东:《新中国以来的甲金文研究》,《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十七辑,2016年。
骈字骞等:《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裘锡圭:《40年来文字学研究的回顾》,《语文建设》1989年第3期。
裘锡圭、沈培:《二十世纪的汉语文字学》,刘坚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宋镇豪:《百年甲骨学论著目》,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
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王宇信等:《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詹鄞鑫:《二十世纪的中国古文字研究综述》,《中国文字研究》第七辑,2006年。
曾宪通:《四十年来古文字学新发现的学问》,刘坚、侯精一主编:《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赵诚:《二十世纪甲骨文研究述要》,书海出版社2006年版。
赵诚:《二十世纪金文研究述要》,书海出版社2003年版。
周有光:《世界文字发展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