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振华(2002:13)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的‘语文学’发展的每一个新成就都是十分重视的。他们对过去的一切语言学遗产,绝不采取虚无主义或全盘否定。恩格斯说:语文学是一门‘内容非常浩瀚的科学’,这样的学科,没有足够的时间,只能一知半解。他们对十九世纪刚刚建立起来的比较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十分敏感,十分重视。”正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以下简称“马恩”)对语文学和语言学的重视并有研究,所以他们能对语言的结构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这里介绍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论语言结构的三个方面内容:(1)语音和语法;(2)语义和词义;(3)语源和词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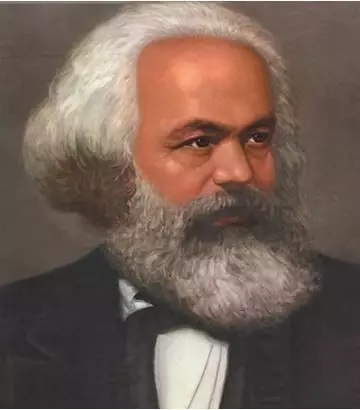
马克思像
1.语音和语法
(1)语音。马恩把语音看作是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一个重要标志:恩格斯(1873)认为,“分音节的语言的发展”把人和猿区分开了。恩格斯(1884)还认为:音节清晰的语言在人类低级阶段产生,也就是“语音”发展的程度是人类“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
经过多少万年的努力,手脚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后终于确定下来,于是人和猿区别开来,于是奠定了分音节的语言的发展和人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这种发展使人和猿之间的鸿沟从此不可逾越了。(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第9卷421页)
低级阶段。这是人类的童年。人还住在自己最初居住的地方,即住在热带的或亚热带的森林中。他们至少是部分地住在树上,只有这样才可以说明,为什么他们在大猛兽中间还能生存。他们以果实、坚果、根作为食物;音节清晰的语言的产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恩格斯,《文集》第4卷33页)
(2)语法。由于马克思懂十多门语言,文法上的错误会马上能看出来,他(1850)说:
在这个独一无二的用不着主语、系词和宾词的句子里犯了一个文法上的大错误。这里应该说:因而处于比你们大家都更有利的条件以便……(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第27卷167页)
恩格斯(1869)精通“古苏格兰文”:
在那段古苏格兰文的摘录中,从语言学观点看,使我感兴趣的只是现在分词havand即“有”这个形式。这部编年史中出现这种形式,这就证明在十六世纪初,也就是说,直到这种形式在英格兰早已消失的时候,它在苏格兰还存在。(恩格斯,《全集》第32卷252页)
2.语义和词义
马恩对词汇有很多论述,如果通读马恩的原著,我们就会看到,由于他们懂多种语言,并且熟练程度很高,他们往往对细小的词义差别都能察觉。下面看两条马恩对词汇的看法:
至于这些“折磨心灵的”和“惊心动魄的”矛盾,如果圣麦克斯不是得到德语中Bürger这个词的帮助,使他能随心所欲地把它一会儿解释为citoyen〔公民〕,一会儿解释为bourgeois〔资产者〕,一会儿解释为德国的“善良市民”,他就决不能制造出这些“折磨心灵的”和“惊心动魄的”矛盾,至少是绝对不敢把它们公开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20页)
俄国农民只是在自己的公社里面生活和活动;其余的整个世界只有在干预他的公社事务时,对于他才是存在的。这一点完全正确,因为在俄文里,весьмир一词既有“世界”的意思,又有“农民公社”的意思。即“全世界”,在农民的语言中就是公社社员大会。因此,特卡乔夫先生说到俄国农民的“世界观”,显然是把俄文мир一词译错了。各个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这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恩格斯,《全集》第18卷618页)
3.语源和词源
马恩对语源和词源是有研究的。“在生命的最后五年中,恩格斯仍然保持着他的语言学兴趣,而且,提出了不少有实际意义的见解。如关于不能把思维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的论点,关于文体学、翻译学的一些意见,关于意义的层次性及词义的科学内涵,以及有关词源学、词汇学、词义学的一些问题”(宋振华 2002:26)。为什么马恩会研究词源,那是因为他们研究某种语言时,同时研究这种语言的历史、文化和文学,因此必然会涉及到词源等问题。“这个时期他们都积极地学习所需要的外语。马克思学西班牙文、瑞典文、丹麦文、意大利文和葡萄牙文;恩格斯研究俄语、斯拉夫语、哥特语、古挪威语和盎格鲁撒克逊语。为了研究东方的历史,恩格斯学了波斯文。他们研究一个民族的语言常常是同研究该民族的历史、文化、文学结合进行的”(宋振华 2002:22)。
下面看几条马恩的论述:
“施蒂纳”在上面驳斥共产主义消灭私有财产这一观点,其办法是:首先把私有财产变为“有”(编者注:德语中Habe,(阴性名词)--财产,所有物;Haben(及物动词)---有,具有。),然后又把“有”这个动词说成是不可缺少的字眼、是永恒真理,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也可能发生施蒂纳“有”胃痛这样的事。现在他也是完全这样地论证私有财产的不可消灭,他把私有财产变为财产的概念,利用Eigentum 〔财产〕和eigen〔自有的〕这两个词的字源学上的联系,把“自有的”这个词说成是永恒真理,因为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也可能发生他“自有”胃痛这样的事。如果不是把共产主义者所要消灭的现实的私有财产变为“财产”的抽象概念,那末,这种在字源学中寻找避难所的谬论,是完全不能成立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53页)
在一切德意志人中是否有一个表示氏族的共同名词,这个名词又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语言的遗迹没有给我们提供答案。在语源上,哥特语的kuni,中部高地德意志语的künne是和希腊语的genos,拉丁语的gens相当的,而且是在相同的意义上来使用的。妇女的名字来自同一个词根,如希腊语的gyne、斯拉夫语的zena、哥特语的qvino,古斯堪的那维亚语的kona,kuna等,这表明曾存在过母权制时代。——在伦巴德人和勃艮第人那里,像刚才说过的,我们看到fǎra一词,这个词被格林假定来源于词根fisan,意即生育,我则倾向于认为它来源于更显而易见的词根faran,意即骑马、游牧、返回,用来表示不言而喻只是由亲属构成的游牧群的某个一定的部分。这个词,在起初是向东方,后来又向西方迁徙的许多世纪中,渐渐地被用来指血族共同体本身了。——其次,哥特语的dibja,盎格鲁撒克逊语的sib,古代高地德意志语的sippia,sippa,都是亲属②的意思。在古代斯堪的那维亚语中,仅有复数的sifjar(亲属)一词;单数只用作女神西芙[Sif]的名字。——最后,在“希尔德布兰德之歌”中还见到另外一种用语,它出现在希尔德布兰德问哈杜布兰德的话中。(恩格斯,《全集》第21卷155页)
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Gemeinwesen》[“公团”],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恩格斯,《全集》第19卷7-8页)
引用文献
宋振华 (2002) 《马克思恩格斯和语言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卫志强主编 (2015)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语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