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r音(rhotic)是世界语言中的一个常见音段,但对于汉语来说,r音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它仅在官话方言中常见,而并不常见于汉语南方方言。例如在吴方言口语中,“儿” 一般读为鼻音声母。但儿缀也是吴方言中的常见词缀,比如在义乌话中,儿缀构词时也会像普通话或者北京话的儿化一样发生音节重组。不过,与北京话儿化加卷舌尾-r不同,义乌话的儿化是加鼻音尾-n。
本文讨论的杭州话的儿缀并不属于吴方言自身的内部演变,而是历史上来自北方方言的r音儿缀在今吴方言中的一个变异。杭州话虽属吴方言太湖片,但由于历史上曾是南宋首都,受大批北方移民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官话色彩。杭州话的独特性之一在于保留了来自北方方言r音儿缀的能产性,这与周边其他吴方言截然不同。杭州话的儿缀属于形态构词层面的儿化,但并不促发语音层面的儿化音变,而是一个独立的音节,并适用广用式连读变调规则。与现今的北京话相比,杭州话的儿缀是存古的,这也印证了宋朝时北方方言的儿缀是自成音节的说法(李思敬,1986)。
本文的重点是杭州话儿缀的语音实现问题。由于吴方言音系中缺乏r音,因此,一般认为这个外来的r音被替换为了边音(赵元任,1928;郑张尚芳,1979;鲍士杰,1988)。因此在文献中,杭州话的儿缀通常被描写为音节化的边音![]() 。但也有争议,史瑞明(1989,1992)认为它是一个r音化的元音。Yue和Hu(2019)则认为杭州话的儿缀是带有r音色彩的边音。本文尝试通过多种发音材料,结合声学研究,综合运用生理与声学实验细节对杭州方言的儿缀进行深度描写,并讨论相关的语音与音系问题。
。但也有争议,史瑞明(1989,1992)认为它是一个r音化的元音。Yue和Hu(2019)则认为杭州话的儿缀是带有r音色彩的边音。本文尝试通过多种发音材料,结合声学研究,综合运用生理与声学实验细节对杭州方言的儿缀进行深度描写,并讨论相关的语音与音系问题。
二、方法
本文材料由三项实验组成:声学实验和两项发音生理实验。声学实验采集了6男6女共12位发音人的语音数据,以中平调的名词词根加儿缀组成测试词。发音生理实验来自同一位男性发音人,均采用名词词根加上儿缀组成有意义的测试词。第一项生理实验是静态舌腭图,通过拍照记录单次发音时的舌腭接触情况,以观察发音部位与发音方式。第二项生理实验是超声与电磁发音仪同步实验。电磁发音仪传感器共设置14个通道点,包括舌尖、舌体、舌背等3个舌面点。超声探头固定在下颌下部正中矢状面方向。
声学共振峰数据与超声、电磁发音仪数据均使用广义加性模型(Wieling,2018)进行统计分析。声学共振峰数据按照性别分组,以标准化后的时间(0-1)为自变量进行共振峰分析。超声影像使用deep lab cut深度算法自动抓取舌型,并以极坐标数值进行舌型对比。电磁发音仪数据以标准化后的时间(0-1)为自变量,以相应的传感器运动数值(如舌尖TTx)为因变量进行分析。
三、结果
3.1 杭州话儿缀目标的声学属性
声学分析结果显示杭州话的儿缀是一个边音,无论前接词根音节的元音类型如何,后接的儿缀都呈现出相似的类中央元音![]() 的共振峰结构。以首二个共振峰F1/F2为坐标的声学元音图进一步证实,单音节词“儿”
的共振峰结构。以首二个共振峰F1/F2为坐标的声学元音图进一步证实,单音节词“儿”![]() 和各种元音环境下的儿缀[-1]的椭圆都占据着类似中央元音
和各种元音环境下的儿缀[-1]的椭圆都占据着类似中央元音![]() 的声学区域并且相互大面积重叠。这种类中央元音的共振峰结构说明杭州话的儿缀是边音
的声学区域并且相互大面积重叠。这种类中央元音的共振峰结构说明杭州话的儿缀是边音![]() 。因此,根据共振峰材料的分析结果看,用一个成音节的边音音段
。因此,根据共振峰材料的分析结果看,用一个成音节的边音音段![]() 来标写杭州话的儿缀是合适的,而没有必要用
来标写杭州话的儿缀是合适的,而没有必要用![]() 。这是因为在声学语音上,[l]与
。这是因为在声学语音上,[l]与![]() 的共振峰结构是类似的,而且,在音系上,
的共振峰结构是类似的,而且,在音系上,![]() 这样的结构是一个例外形式,无端增加了杭州话音系的复杂性。
这样的结构是一个例外形式,无端增加了杭州话音系的复杂性。
3.2 杭州话儿缀的发音生理属性
静态舌腭图支持声学分析结果,作为边音![]() 的“儿”的舌腭接触仅存在于矢状面位置的正中位置,表明其发音方式是一个边音,正中阻塞,气流从两侧通过。
的“儿”的舌腭接触仅存在于矢状面位置的正中位置,表明其发音方式是一个边音,正中阻塞,气流从两侧通过。
超声影像则揭示了整个动态发音过程。杭州话儿缀[-1]的发音涉及一个清楚的舌尖抬起动作,是一个从前接目标元音舌位向中性舌位回归的过程,近似于汉语普通话或美式英语中r音化的发音。在此过程中,舌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于舌体的发音器官向其齿龈或齿龈后的目标位接近。例如,在后高元音[u-]或低元音[a-]后接儿缀时,舌体回复中性的动作和舌尖动作都相当明显。因此,杭州话的儿缀可以用卷舌变音符号![]() 来标写。
来标写。
3.3 儿缀对前接词根音节元音的影响
杭州话的儿缀对前接词根音节有两个影响。首先是杭州话的儿缀促使两个降峰双元音[ei ou]在儿缀词中的频谱动态性消失,实现为单元音[e o]。其次是典型的r音性,也就是杭州话的儿缀[1]会引发前接词根音节元音的第三共振峰显著下降。这一下降在前接元音的前40%时间段便开始。F3的显著下降是r音化的典型声学特性,这从声学上证实了杭州话儿缀的发音具有r音性。电磁发音仪(EMA)的动态分析进一步探究了这一现象所对应的发音动作,结果显示F3的下降与舌尖传感器的抬起和后缩(TTz和TTx的运动)高度相关。
四、结论
因此,杭州方言的“儿”既是一个边音,也是一个r音,应该记作卷舌边音![]() ,是边音音位/l/在自成音节或作为词缀时的一个变体。而且,作为儿缀的时候,它更倾向于是一个r音,舌尖动作促发前接词根音节的元音的r音化,只是在发音的末尾带有短暂且不太稳定的边音[l]。这解释了史瑞明(1989,1992)作为美式英语母语者将其描写为一个与美式英语r音相似的音而不是边音的原因。结合历时接触音变的角度,杭州方言就是用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将一个外来权威官话的r音,在保留其发音与声学特性的同时,实现为了其自身吴语音系中存在的边音音位/l/。通过本文提供的发音与声学语音的细节,我们得以观察到这种语音与音系的接触与融合。杭州方言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极具个性的方式,成功吸纳了接触音变,实现了吴语方言借用来自历史上权威官话的儿缀构词过程,成为其自身方言的语法的有机组成部分,至今仍焕发着生命力。
,是边音音位/l/在自成音节或作为词缀时的一个变体。而且,作为儿缀的时候,它更倾向于是一个r音,舌尖动作促发前接词根音节的元音的r音化,只是在发音的末尾带有短暂且不太稳定的边音[l]。这解释了史瑞明(1989,1992)作为美式英语母语者将其描写为一个与美式英语r音相似的音而不是边音的原因。结合历时接触音变的角度,杭州方言就是用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将一个外来权威官话的r音,在保留其发音与声学特性的同时,实现为了其自身吴语音系中存在的边音音位/l/。通过本文提供的发音与声学语音的细节,我们得以观察到这种语音与音系的接触与融合。杭州方言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极具个性的方式,成功吸纳了接触音变,实现了吴语方言借用来自历史上权威官话的儿缀构词过程,成为其自身方言的语法的有机组成部分,至今仍焕发着生命力。
部分参考文献
鲍士杰 1998 《杭州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李思敬 1986 《汉语“儿”![]() 音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音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史瑞明 1989 《杭州方言里儿尾的发音》,《方言》第3期,180-181页。
徐越 2002 《杭州方言儿缀词研究》,《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93-97页。
赵元任 1928《现代吴语的研究》,清华研究院丛书第四种。
郑张尚芳 1979 《温州方言的儿尾》,《方言》第3期。
Simmons, Richard VanNess (史瑞明,现称史浩元) (1992). The Hangzhou Dialect.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Wieling, Martijn.(2018). Analyzing dynamic phonetic data using generalized additive mixed modeling: A tutorial focusing on articulatory differences between L1 and L2 speakers of English. Journal of Phonetics, 70, 86–116.
Yue, Yang and Fang Hu (2019).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of the -er suffix in the Hangzhou Wu Chinese dialect. Proceedings of 19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honetic Sciences (ICPhS 2019), 2056-2060, Melbourne, Australia.
作者介绍
胡方,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语言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语音学研究,近年来主要工作一方面着重于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描写汉语及相关方言、语言中的语音现象,另一方面则着眼于在人类语言的语音多样性中寻找普遍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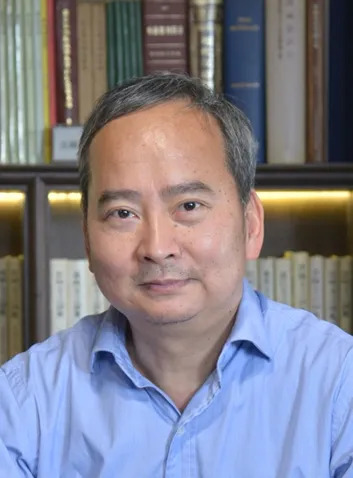
岳暘,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学术专长是语音学,研究兴趣是通过发音实验手段描写汉语方言及相关世界语言的特定现象,并进一步探究这些共时现象与历时音变的潜在关联,在包括《中国语文》、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Accept)等在内的国内外学术期刊、会议发表论文多篇。

原文刊于《中国语文》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