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考察上古汉语中连接两个NP的“与”的句法和语义。前人往往将“与”对译为现代汉语的“和”或英语的and,并定性为并列连词(杨伯峻,1981等)。本文则提供一种动词分析的视角,认为一些句法环境和语境中的“与”有可能是动词。
胡建华(2021)将下例中的“与”分析为“随、从”义的动词。
(1)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
(2)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维士i与女j,伊其相谑,pro i赠之j以勺药。(《诗经·郑风·溱洧》)
胡建华重点分析了“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认为“与”的语义是“跟随、追随、会同”,其结构不是两个NP的并列结构,而是“主动宾”结构,故“与”前后的NP不可互换位置,否则就失去了以溱水汇入洧水比喻男子追随而来与女子相会这一比兴意义。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指出,“维士与女”中的“与”同样是“跟随、追随、会同”义动词。首先,“pro i赠之j以勺药”的空主语pro只能回指“士”(代词“之”指称的是“女”),而不能回指“士与女”整体,否则就会造成句中NP指称的混乱,以致错误理解句意。其次,假设“维士与女”中的“士与女”是两个NP的并列结构,它们理应可以互换位置而保持句意不变;但实际上,由于“赠之以勺药”中的施事NP(pro,回指“士”)、目标NP(“之”,指称“女”)是确定的、不可改变的,一旦两个NP互换位置,就会导致句子原本的语义彻底改变。
胡建华(2021)针对这些例证提出的“随、从”义动词分析是十分合理的,不过,为了解释更多的例证,还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动词“与”的语义发展路径。本文认为,动词“与”的语义发展路径大致如下所示:
“共举”→“共事、协作”(→“共同&作为”)→“会同、偕同、相与”
在具体的语境下,可由“与”的基本(primary)语义“会同、偕同、相与”推导出具体的语境义(contextual meaning)。“会同、偕同、相与”义的动词“与”要求两个论元,二者不仅承载着不同的题元角色,而且作为事件参与者,在很多情况下地位不平等,往往有主次之分,故“与”前后的NP理应不可互换位置。“会同、偕同、相与”义的“与”,可以是主者“与”次者(例:校长会同/加入青年学子),也可以是次者“与”主者(例:士兵会同/加入部队)。正因如此,“会同、偕同、相与”这一基本语义在不同的语境下可以推导出不同的语境义。
1. “NP1之与NP2”和“NP1与NP2”
“与”不仅可以构成普通主谓结构“NP1与NP2”,还可以构成“主之谓”结构“NP1之与NP2”。
(3)夫吴之与越也,仇雠敌战之国也。(《国语·越语上》)
“主之谓”本身的结构特性决定了“NP1之与NP2”中的“与”只能分析为动词,而无法分析为并列连词(以及介词);与之表达相同语义的普通主谓结构“NP1与NP2”中的“与”,也应分析为动词。动词“与”的基本语义是“会同、偕同、相与”,在相关句法环境和语境中推导出两个NP“相与”或“偕同”构成某种关系的语境义。
(4)其礼曰:“丧父母三年,妻、后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戚族人五月。”若以亲疏为岁月之数,则亲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后子与父同也。(《墨子·非儒下》)
(4)先讲为父母服丧的时限,并以此为参照比较为不同亲属服丧的时限,因此,NP1是比较项,NP2是参照项,故两个NP不可互换位置,否则不符合话语逻辑。
我们还可以通过“与”前NP为零形式代词pro的例证,进一步说明动词分析更为合理。
(5)……不应不动,则上下无以相有也。若是i,则pro i与无上同也,不祥莫大焉。(《荀子·正论》)
首先,(5)中“与”前后的NP都是无生命的,而以无生命NP作为“与”的前后项,可以排除其伴随义介词解读(杨萌萌、胡建华,2024)。其次,“与”前的NP为pro,而且“pro与无上同”是“则”引导的分句,在这种情况下,“与”无法分析为并列连词。
2. “唯NP1与NP2”
“NP1与NP2”可以出现在“唯(惟)”字强调句中。在有些情况下,“唯”强调的并不是“NP1与NP2”整体,而是仅强调NP1,此时“与”不能分析为并列连词,而是应分析为动词。
(6)既,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县、繁缨以朝。许之。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左传·成公二年》)
“仲尼”所言是围绕“请曲县、繁缨以朝。许之”事件展开的,谈论的核心是“器”,且仅仅是“器”。在“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中,“唯”强调的只是“器”。假如认为所强调的是“器与名”,那么“器”与“名”理应可以互换位置。但是,倘若此句变为“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显然与上下文语境不符,也达不到语篇连贯的要求,因为当前话语围绕“器”展开,在未提及“名”的情况下,不应该突兀地强调“器”和“名”二者或二者构成的并列结构。
本文认为,“器”指礼器,“名”指名分,即封号;在以“器”为谈论的核心、仅强调“器”的这一语境下,“与”不能分析为并列连词,而是应分析为动词。在动词分析的视角下,本文为“与”提出两种可能的语境义分析。第一种分析是,动词“与”在当前语境下可以推导出“随、从”语境义。此句可理解为:器,(是)随从名(的),不可以假人(不可以给没有名分/封号的人)。第二种分析是,在仲尼的话语中,“器”是谈论的核心,“名”是附带谈论的对象(可理解为后追加的谈论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动词“与”推导出“连带、附带、携带、连同”义,近似于现代汉语的“还有”。此句可理解为:器,连同/还有名,不可以假人。
3. “V+NP1与NP2”
(7)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
动后位置上的“与”往往更容易对译为“和/and”义并列连词。本文也赞成(7)中的“与”可以分析为并列连词。但是,如果说它只能分析为并列连词,则过于绝对。本文强调,对于这类“V+NP1与NP2”结构,将“与”看作并列连词,仅是作出一种可能的分析;而将“与”分析为动词,同样也可以疏通其句法语义。
在“与”是动词的思路下,可为(7)中的“与”提供三种可能的语境义解读:一是“随、从”义,二是指示两个NP构成某种关系的“相与”义,三是“连带、附带、携带、连同”义(此时的“与”近似于现代汉语的“还有”)。相比之下,前两种方案的解释力有限。按照第三种分析,(7)可大致解读为:夫子谈论性连同/还有天道,不可得而闻。“言性与天道”是一个含次谓语(secondary predicate;SP)的复杂VP结构,即[V NP SP],“与”是次谓语SP的中心语;在语义上,SP对它前面的NP进行追加陈述(杨萌萌、胡建华,2018)。
4. 结语:动词“与”何以表达并列义?
在上古汉语中,一些句法环境和语境中的“与”应当(或可以)分析为动词。动词“与”之所以在今人的一般理解中表达并列义,并对译为“和/and”义并列连词,是由基于特定语境义的语义衍生以及现代汉语语感影响这两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在具体的语境下,可由“会同、偕同、相与”这一动词基本语义推导出“随、从”义,“连带、附带、携带、连同”义,指示两个NP构成某种关系的“相与”义,由此很容易衍生出较笼统的一个NP与另一NP共同作为之义;这一衍生性的(secondary)语义解读,则进一步理解为类似于“和/and”的并列义。
由于现代汉语语感的介入和影响,容易将在适当语境下可衍生出笼统的并列义的“与”直接对译为“和”,并认为“与”是像“和”一样的并列义虚词。之所以如此,大概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由于现代汉语常以“和”等并列义虚词连接两个NP,因而很容易忽略动词其实也可以形成NP并列义结构。第二,由上古汉语“与”发展而来的现代汉语“与”已是虚词,若忽视历史来源和历时演变而看待“与”,很容易将古今两个“与”等同,都视为虚词。
本文最后强调,上古汉语句法与现代汉语句法在诸多方面表现出显著差异,研究包括NP并列义结构在内的上古汉语句法问题,务求避免、摆脱现代汉语语感的介入和影响,对相关句法结构或现象作出符合一般句法原则且与上古汉语句法系统相适配的分析。
参考文献
胡建华 2021 《〈秦风·无衣〉篇诗句的句法语义及其他——对一种以并联法为重要造句手段的动词型语言的个案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杨伯峻 1981 《古汉语虚词》,中华书局。
杨萌萌 胡建华 2018 《“和”的句法》,《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杨萌萌 胡建华 2024 《汉语NP并列词的微观差异》,《辞书研究》第6期。
作者简介
杨萌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生导师,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Visiting Scholar,2021-2022)。主要研究方向为句法学、语义学、上古汉语语法、历史语言学。2018年获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青年学者奖。代表作:《语法中的显著性与局部性:Wh疑问句与反身代词的句法和语义》(独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4年);《“主而谓”结构的句法》(《当代语言学》2025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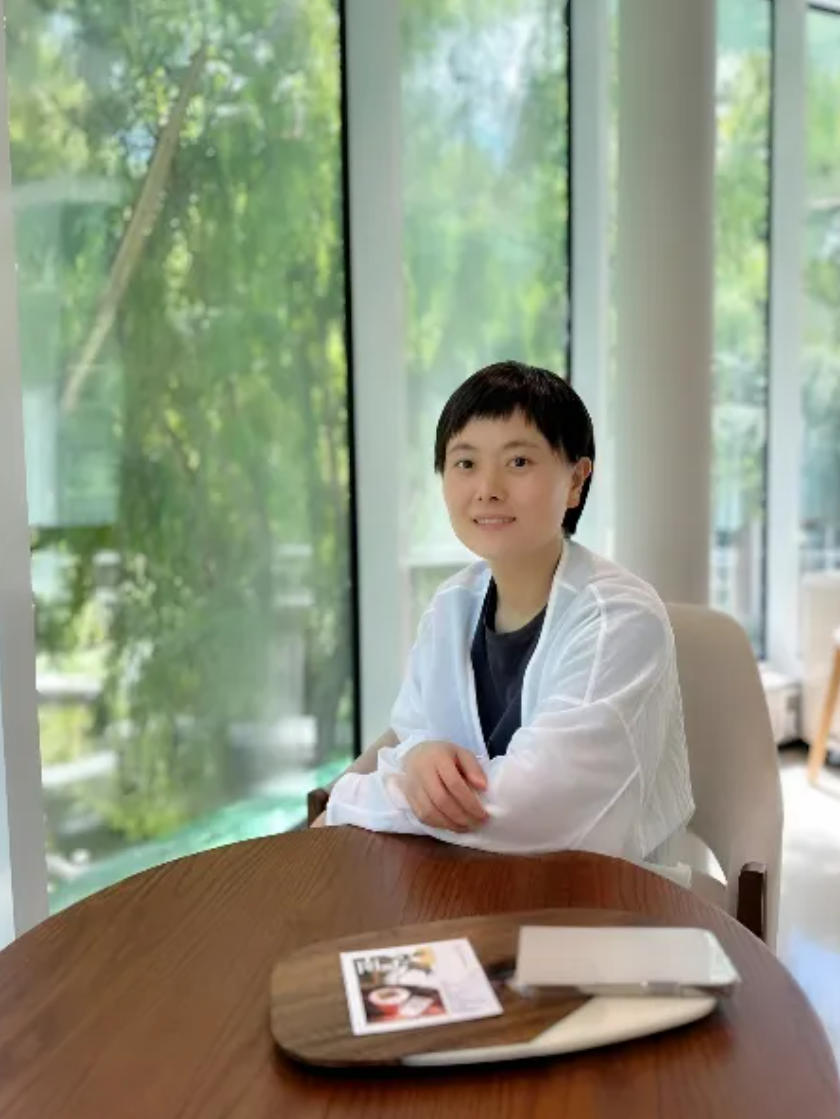
原文刊于《中国语文》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