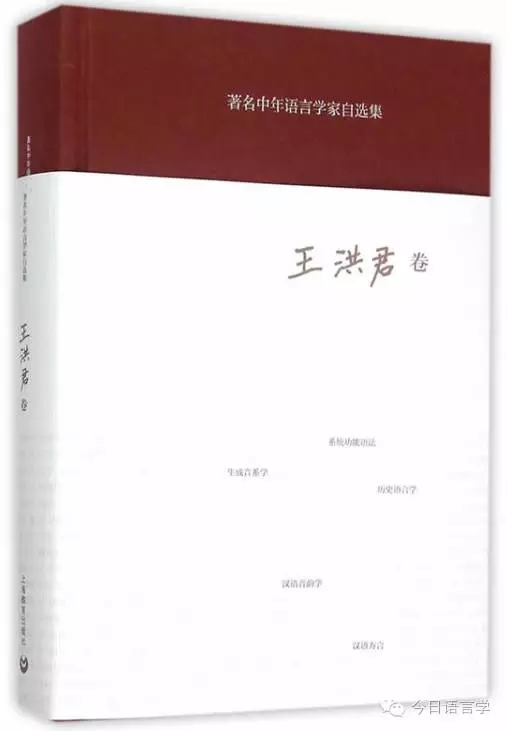徐通锵先生提倡字本位说的第一篇文章是1991年的《语义句法刍议》,那时我早就硕士毕业,并刚在美国学习了新的音系学理论回国,全部心思都在音系学的方面,对徐老师新的研究思路不太理解。后来开始支持徐先生的字本位,一个是遇到一个机缘,袁毓林老师当时还在清华,为纪念赵元任先生诞辰100周年,于1992年组织赵元任先生翻译用英语发表的语言学论文,结成文集作为清华文丛之四出版,分配我翻译其中的《汉语词的概念及其结构和节奏》一文,题目中的“词”其实应该是加引号的,因为全文中赵先生阐述的都是,从语言系统来看,汉语中的“字”才是相当于英语中“词”的单位。为避免术语的干扰,赵先生先把汉语单音节的“字”用“音节-词”来表示,多音节的“词”用“结构词”来表示。文章的最后一段,我的翻译是“按西方语言学家的眼光来分析汉语并确定像结构词这样的单位可能有用:一方面跟音节词的“字”区分开来,另一方面跟短语和句子区分开来。我想这样做是有用的,并且一直在试着做。但这不是汉人想问题的方式,汉语是不计词的,至少直到最近还是如此。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字”是中心主题,“词”则在许多不同的意义上都是辅助性的副题,节奏给汉语裁定了这一样式。”读了这篇文章,我被赵先生大量的实例和透彻的说理说服,从此开始支持字本位。二是前面说过的,我的音系学研究和现代汉语词法研究,包括参与信息处理学界“词切分”和“信息处理用词库”工程的实践,都进一步指向字本位是汉语文大系统的特点。
这段翻译,还有个质疑我一直没有答复。这就是有学者认为其中的“汉语是不计词的”是误译,这一说法还为其他不少学者所引用。在这里我顺便说下我的意见。这一整句的英文原文是But this is not the Chinese way of thinking, at least until recent times, which don’t count. 我以为翻译的关键有二,一是which指代的是什么,二是don’t count怎么译。从上下文看,我认为这句句首的it和后面的which的所指是相同的,都是指前面的“按西方语言学家的眼光来分析汉语并确定像结构词这样的单位可能有用:一方面跟音节词的‘字’区分开来,另一方面跟短语和句子区分开来。我想这样做是有用的,并且一直在试着做。(但这不是汉人想问题的方式,……)”,特别是其中的“按西方语言家的眼光分析出来的、类似英语中‘词’那样的单位”,它不是the Chinese way of thinking,它don’t count。然后是don’t count如何译。我考虑,count在英语中的本义是“计算”“按某种单位来数数”,don’t count则有引申义“不把××计算在内”“认为××是不重要的,可忽略的”;而汉语的“不计”,也有“不按某种单位来数数”和“不把××计算在内”“认为××是不重要的,可忽略的”的双重意义,因而选择了“汉语是不计词”的翻译。叶蜚声老师详细校对了我的翻译,对这一段没有提出异议,只是感叹道“赵先生到老年糊涂了!”姜望琪老师认为“你应该直接译为‘汉语中词是不重要的’”,沈家煊老师则认为我的翻译很好。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对于理解赵先生本义和字本位都是很重要的,最近还是要抽时间答复一下。
从另一个角度看,贯通这三个领域,再加上语篇领域,一个总的思路是,立足汉语追求人类语言的普遍性。立足汉语是说首先要根据简明性原则建立适合于分析描写汉语的语言模型,追求人类语言的普遍性是说根据汉语的特点找到的模型要放到人类语言更大的环境中再考察,具体语言层次上的特殊性放到人类语言的高层次上,也只是高层次普遍性的一种具体体现。比如汉语的“字”和英语的“词”在更高层次上都是语言音系单位与语法单位的交会,只是交会的层级有高低不同;再比如说汉语和英语的音节都可以首先分为声、韵两大成分,只是汉语的声韵两成分主要体现为整齐的替换和搭配格局而英语声韵两成分主要体现为与词重音的位置是否相关。
总的来说,立足汉语追求人类语言的普遍性只是我的追求,由于个人功底的局限,特别是中国传统小学和英文的功底不足,会直接影响到自己对汉语语料的分析和对国外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以上的简单介绍也一定多有井中之蛙的自大之处,说出来便于大家多多指正。
乐耀:谈谈对您影响最深的一位或几位老师。
王洪君:对我影响最深的是我的硕士导师徐通锵先生。于学问上,是他引领我进入历史语言学研究领域,是他倡导字本位理论启发我更早地梳理出汉语音系格局的控制基点在“单字音”,他以身作则让我懂得了研究理论必须立足材料,立足汉语;让我懂得了理论的重要性:材料总是繁杂的、个别的,理论总是简明的、普遍的;有了理论的框架和视角,材料才从繁杂、散乱、混沌一团中显示出格局和规则。于品德上,他潜心学问,治学认真,反感对场面上的应酬。他对不拿礼物前来请教问题的学生极其热情,对拿了礼物、说赞扬之辞的来客却把不悦之情直接溢于言表。我们俩共同做的研究,他执笔写的论文总是署上我的名字,而我执笔写的论文他从来不署自己的名字。他从来没有组织过学术会议,从来不出祝寿文集,也没有在各种学术团体中担任职务。他仅拿过两次教育部的科研基金,一次1万元,一次1.8万元。他给学界留下的是6部专著、两部论文集和70余篇论文。他给我和同门留下的,是正直的风骨、求知的大智慧、悉心培育的深情和殷切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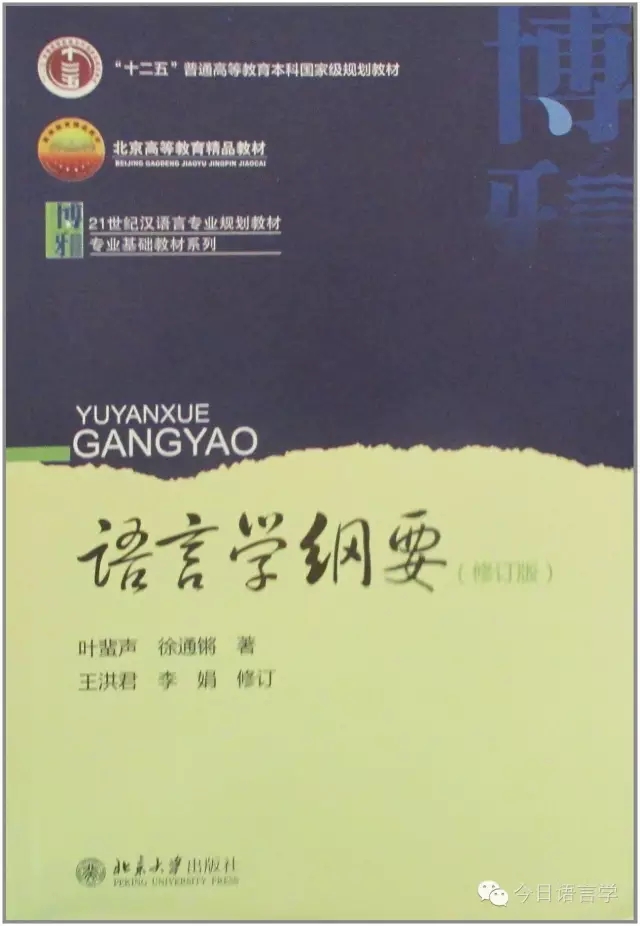
再就是王福堂先生。他的耿直、纯真、对学问的执着和严谨、对名利的淡泊带给我心灵上的沉静。这种影响是更深层次的,对我来说,学术上的每一步前进都离不开心灵上的沉静;或者说,心灵上的沉静比学术上的进步更为重要。

王洪君老师与爱人王福堂教授(右)
乐耀:您对如何培养青年语言学学者有什么建议?对青年学者有什么期望?
王洪君:这个问题我可没什么值得说的。你是我的学生,知道我的一个突出弱点就是完全没有领导能力,可能跟我是家中老小有关吧,我从小就没有领导能力,对别人完全没有要求,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培养青年学者。北大的教务部或学生的什么团体也曾希望采访我,让我谈谈培养研究生的经验。我连说不行,我只是放羊式管理,学生对哪个方面有兴趣,就任他往那个方向发展。
对刊物或单位想说的是,多发些青年学者的文章,多组织一些青年学者的高端论坛。
对青年学者想说的是,首先是要认清自己适合做什么,像我就完全没有从政或做经济、法律等工作的能力和素质;其次是自己适合做的、有兴趣的,就坚持下去;如果工作需要、团队需要,小的领域不妨换一换,我上大学已经28岁,硕士毕业34岁,之后还换过或跨过几个研究方向。你们年轻,潜力更大,跨方向的研究、为团队服务的研究也许一时难于很快出成果,但人不可太计较,如老子所言,“无私”方可“成其私”,跨方向的研究、为团队服务的研究不但是人生的丰富,后来也多半会用得上。
要争取每年开一两次会,发一两篇文章,不要太多也不要自己一人闷头做学问。学问学问,就是志同道合的一群人彼此问答的产物,有交锋才有火花。
不多说了,这世界变化快,我的经历和想法在现在的世界会有多大的参考价值?仅希望青年学者能够从非世俗的研究中发现属于自己的快乐,得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乐耀:最后一个问题,谈谈您对我国语言学研究发展的展望。
王洪君:我水平有限,对国内外语言学及相关学科的最近发展了解不多,不敢妄谈展望,就说说我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新成果吧。希望看到:⑴立足于汉语的材料,最好是包括古今汉语、或不同汉语方言或相邻其他民族语言、或外国人学习汉语、计算机处理汉语等方面的材料,根据大量的材料而抽象出的描写分析汉语的新模型,比如宋柔老师多年前提出并在2亿字节语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两字结构库,他最近几年提出的处理汉语语篇的堆栈模型和广义话题论;万业馨老师最近获得的德语地区出版奖(Friedhelm-Denninghaus-Preis,典宁豪斯奖)的对外汉语用汉字教材及教师用书;⑵所建立的汉语模型,希望能够充分吸取中国传统小学或文章学的精华,比如他们的视角和术语体系;⑶所建立的汉语模型,还希望也能够对人类语言模型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