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定一(1913年11月——2013年1月),笔名周因梦、因梦、许令芳、尹梦华等,湖南酃县(现炎陵县)人,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35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39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先后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和北京大学。1950年调入刚组建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先后担任《中国语文》杂志常务编委、《现代汉语词典》编审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近代汉语研究室主任,并兼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市语言学会副会长等职务,曾任民进中央学习委员会委员。
编者按
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计划编纂出版一套《学问有道》丛书,内容是请社科院的学部委员和荣誉学部委员谈人生和治学经验。于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学研究二室祖生利研究员采访了周定一先生。
2007年3月28日一个温暖的下午,94岁高龄的院荣誉学部委员、语言所研究员周定一先生在他的家里接受了笔者的访谈。周先生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锐,面对笔者的提问,用略带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徐徐而谈。先生的记忆力非凡,那一桩桩跨越了大半个世纪的久远往事,竟然至今记忆犹新。我手中的笔不停地记录着。天色将晚,而我准备的访谈提纲才进行不到一半。为了不致先生太过劳累,我起身告辞,并跟先生约定好下一次访谈的时间。就这样前后去了先生寓所三次,才最终完成了访谈任务。
祖生利(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学研究二室,研究员。以下简称祖):周先生,您好!非常荣幸能跟您做这样的一次访谈,有机会聆听您的教诲。作为一位世纪老人,您的人生阅历一定非常丰富。能否先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的人生道路?
周定一(以下简称周):好的。我1913年11月生于湖南酃县(现改称炎陵县),井冈山西麓的一个小县城。我父亲是上海交大毕业的,长期在铁路上当工程师。幼年时我先在家里念了几年私塾,后来在长沙读完小学和初中。初中毕业后,因为父亲工作的变动,我到上海浦东去读高中。念了不到半年,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我便转到南京的中央大学实验中学。1934年我高中毕业,先是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的“备取生”,不巧那一年师大国文系没有空余的名额,只好回到南京,在中央大学国文系旁听。后来跑到扬州参加扬州中学举办的一个高考补习班,在那里补习了半个学期。1935年初夏,我下定决心又到北京来考试,这一次同时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北师大国文系。因为是北大先放榜,所以也就上了北大(许多年以后,我碰到黎锦熙先生,跟他谈起当年两次考师大的事,说差点儿做了他的学生)。1935年秋,我到北大中文系读书,校址在沙滩红楼。念完二年级,抗战全面爆发,北大和清华、南开合并后南迁长沙,不久又迁到云南,组建为西南联合大学。1939年我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先是在云南大理中学、昆明中法中学教了两年多国文。1942年,联大中文系聘我做助教,后来又成为教员(职位低于讲师,但高于助教)。这段时间主要与沈从文先生合教大一的国文,直到抗战结束,受北大中文系之聘,回到沙滩故校。后转入北大文科研究所。1950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我调到语言所,成为最早来所的一批研究人员之一,此后便一直没有离开过语言所。50年代,我在语言所干得最久的工作是编辑《中国语文》,为最初的九名编委之一。1955年底,我以常务编委身份主持《中国语文》编辑部的日常工作,一直干到1960年底。后来我调到汉语史研究室,从事汉语史的研究工作。1969年底,语言所全体下放河南息县,我在干校的菜园子里当了两年的“菜农”,直到1972年夏天才随部所返回北京。“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年所里学科调整,我被任命为近代汉语研究室主任。1987年我从语言所退休。
祖:据晚辈所知,您不仅是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年轻时还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作家和诗人,您曾经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西南联大“南湖诗社”的重要成员。能否请您谈谈您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和语言学研究道路的?
周:我是怎么走上文学道路的,过程很复杂。我父亲是学工的,我小的时候家里有的只是些关于铁路机械方面的书籍,并没有什么文学方面的藏书,只有一部石印的残缺不全的《三国演义》。我就一知半解地翻看,也许无形中得到许多好处。我念私塾的时候,父亲从外地寄回来一套《国民小学国文课本》,共八册。这是一套新式的语文课本,用浅近的文字编写,编得很好,很实用,从“人、手、足、刀、尺”读起,由浅入深。这套教科书在当时相当流行。记得里面有许多对句,如“窗前、阶下”、“红花、绿叶”之类,朗朗上口,易于理解和记诵,直到今天我还能背诵其中的某些段落。(按:说着,先生便随口背诵起第七册中一篇讲述岳飞抗金的文字:“[金人]拐子马相联,一马仆,二马不能行。[岳]飞挥军进击,大破之……”)我那几年在私塾学的便是这个,可以说打下了较好的文学底子,后来转到长沙去上小学,学校附近就是湖南省立图书馆。馆内图书设有儿童部,我就每个礼拜一有空就到那儿去看书。那个时候儿童可看的书籍实际上很少,没用上半个学期,儿童部的图书就被我读完了。等进了初中,虽然国文课上老师讲授的还都是些文言文,但这个时候新文学运动已经蓬勃兴起,学生们课余喜欢看的多是些白话小说。记得我头一次读到鲁迅先生的《呐喊》和《彷徨》,还有郁达夫等人的小说时,兴奋不已,仿佛一下子被带入一个崭新的世界里。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我从上海转到南京中央大学实验中学,那是所很好的学校。当时教我们国文的是常任侠先生,中央大学国文系出身,是位有名的新诗人,旧学根底也非常好。他很器重我。我原本念的是理科(因为父亲的关系),物理和数学也学得不错,后来之所以喜欢上了写作,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常先生的影响。我最早发表在《中央日报》副刊上的是一篇散文,题目叫什么已经忘了。当时的副刊编辑是储安平先生,他跟常先生很熟,过后他请常先生给我捎话,让我去领稿酬,常先生才知道我发表了文章。这以后,我又和几位高中同好一起办了个文学刊物,名字叫《春野》,一共出了三期。为此,还在《中央日报》上发了篇通讯,虽然只有豆腐干大小的篇幅,可是受到很大的鼓舞。常先生教了我两年半国文,使我获益匪浅。至今我所能记诵的诗词古文,多半都是常先生教会的。新中国成立后,常先生在中央美院当教授,一直到去世。
上大学后,教我们写作的是废名(冯文炳)先生。废名推崇的是周作人那一派的散文,加上他自己的独特风格。我本来写文章很狂放,“下笔不能自休”。后来受了废名的影响,收敛了许多,追求所谓言外之意,小而精,但毛病是不免拘谨。抗战爆发前,废名与周作人在《世界日报》上办了个栏目,叫《明珠》,我在那上面曾经发过几篇文章,有点迎合废名的风格。到了西南联大后,我们一班喜好诗文的学生,有穆旦、向长清、刘兆吉,赵瑞蕻、刘重德、林蒲、刘绶松、陈三苏等,在闻一多先生和朱自清先生的关心下,成立了“南湖诗社”(当时联大文法学院设在蒙自的南湖边上,因此得名)。这是联大最早成立的学生诗社。在蒙自待了一学期,文法学院搬回昆明城里,诗社又改名“高原文艺社”等。在联大中文系老师中,有位杨振声先生,我选修他的“新文学研究”课(在大学里开设这门课,杨先生可是第一人)。我的习作杨先生比较赞许,介绍到《大公报》等报刊上去发表。抗战结束后,我从昆明回到北京,在北大中文系教书期间,沈从文先生让我协助他编《平明日报》(此报后台是傅作义)的副刊《星期艺文》(该刊的发刊词是我执笔写的)。开始是沈先生一个人署名,二十期以后我们共同署名,一共编了一百期,直到北京快解放。
总之,我对文学虽然喜好,却没什么大的成就,基本属于“玩票”性质。1950年,我被调入语言所后,主要兴趣便转到语言学方面来了。不过,我倒也没有全然放弃过文学的写作,经常写些随笔短文和纪念文章之类,可以说仍是“脚踏两只船”。后来编《红楼梦语言词典》,也因为语言和文学是相通的。
至于说我又是怎样走上语言学研究的道路的,这跟罗常培先生有很大的关系。我虽然从高中时就偏爱文学,但在北大二年级分科时,选的却是语言文字学科。文学和语言本来就是两兄弟,互相依赖的。那个时候,罗常培先生和魏建功先生教我们音韵学,唐兰先生教古文字学,沈兼士先生教文字学。特别是罗先生,对我的指导作用很大。比如,因为我是客家人,罗先生对客家话很感兴趣,就经常提醒我注意自己的客家话。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关于家乡客家话的,曾得到罗先生的赞许。这篇文章后来一直没有完整发表过,手稿至今还搁在那里。此后,我在联大和北大中文系任教,后来又到北大文科研究所,罗先生一直是我的师长兼领导。1950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我跟随罗先生一起来到语言所,罗先生当时任所长,我仍是在他的领导下工作,直到1958年他故去。我虽然没有走罗先生治音韵学的路,但正是他引领我走上语言学研究道路的。
我在语言所开始的第一项研究,是“近百年汉语词汇演变研究”。那是1950年,根据中央有关领导的指示,要求语言所组织人马研究自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近百年的词汇演变。我和其他几位同志奉命承担了这项工作,从搜集原始资料开始入手,搜集了不少清末民初的资料。那时语言所和近代史所是邻居,我就到近代史所去借阅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的老《申报》,那上面有很多近百年来产生的新词。可是工作进行到一半,忽然接到命令,专题撤销了,人员派作他用,手里的资料也因之分散了。不过这时期摸材料的功夫并没有白费,使我对汉语词汇的演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有了初步的认识。日后我以词汇研究为主攻方向,应该说是从“近百年汉语词汇演变研究”项目起步的。
1952年,《中国语文》创刊,我被调去编《中国语文》,后来做常务编委,并负责编辑部的日常工作。这段时期,除了花费大量精力编杂志外,我还发表了一些研究性的文章。我还结合当时国家语言文字工作需要,写了不少普及汉语知识、宣传语言规范和文字改革的文章。1958年,《现代汉语词典》开始编纂。到1960年,推出词典“试印本”,我是试印本的审订委员之一,为审订这部词典最初的稿件花了不少时间。1960年底,我离开《中国语文》,被调到汉语史研究室。起初是承担了集体项目《汉语语音史》的“现代语音”部分,但这个项目后来又中途停止了。我又去协同谭全基先生修订郑奠先生负责编集的古汉语修辞学资料,费时一年多,将八十多万字的原稿删削为四十多万字的定稿,而且对引用的每一条资料都查对了原书。后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这本书我没有列名,只写了一个后记。有人对这样处理感到疑惑,其实我那是真心实意的)。1972年从河南干校回来,我又被调去参加修订《现代汉语词典》。在那个事事强调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年代,我们经常跑去外地厂矿征求工人们对于词典条目的意见(当时不得不这样)。1978年,《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发行。如今,最初的试印本的审订委员们都已驾鹤西去,只剩我一人还活在世上。
1977年,所里学科调整,我担任近代汉语室主任。时值“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百废待兴。我就跟本室钟兆华先生商量合作研究《红楼梦》的词汇。起初只是以“《红楼梦》词汇研究”为题进行一些专题研究,并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后来材料积累得多了,就萌生出编著《红楼梦语言词典》的打算。于是从底本文字的校勘开始,设计体例、选定词条、排比例句、归纳义项。到1981年,前八十回词条的初稿完成。这时,我的研究生(也是唯一的)白维国同志也参加进来,主要负责后四十回条目的编写。1983年,整部词典的初稿完成。我又逐条修改,再交钟兆华先生复核。前后修改好多遍,直至1988年才最终定稿。1995年,《红楼梦语言词典》,终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曹雪芹曾说自己写《红楼梦》,是“十年辛苦不寻常”,我们这部词典也编了差不多十年,“个中甘苦只心知”。1987年,我从语言所退休,但学术研究工作并没有终止,陆续发表了若干词汇、语音、语法和方言方面的专题论文。此外还负责罗常培先生文集的搜集整理,编写了罗先生的著作年表;撰写了多篇回忆和纪念语言学界师友的文章,这些文章有的已经发表,有的尚未发表。
祖:您在文学和语言学领域长期辛勤耕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出成就。能否请您总结一下自己在文学和语言学方面的主要成就和贡献?
周:我在文学方面,没有取得什么惊人的成绩。我的文学成果不算多,主要是新诗和散文,旧体诗较少,大多发表于战乱年代的报纸杂志上,我自己保存下来的也已经不多。其中有些篇目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至今还辗转为别人所提及。我在西南联大组织和参加了“南湖诗社”,是其中的主要成员之一,这个诗社的创作活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像穆旦他们已经是载入史册的人物了。抗战结束后,我和沈从文先生在北京合编《平明日报·星期艺文》,以发现和培养“新生代”作家为己任,努力扶持“新一代文学创作”,提携了许多文学新人,最年轻的只有十多岁,像著名诗人邵燕祥,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才十三四岁的光景。我还写过不少纪念和回忆师友及所亲历的重要事件的文章,这些文字兼有文学和学术的性质,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我在语言学方面的著述也不是特别多。不过语音、词汇、语法、方言、语言学史、词典编纂、语言政策和文字规范化等,都有涉猎。其中用力最多的是词汇,特别是近代汉语的词汇研究。下面我择要谈几篇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
1.《对〈审音表〉的体会》(1965)。这篇文章主要讨论《审音表》(即《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中国科学院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撰,文字改革出版社,1963年)对于北京话异读字的审音处理问题。文章指出需区别北京话异读字的不同性质,并采取相应的审音策略,包括订音、注音和正音。文章还谈了对《审音表》的“审音以词为对象、不以字为对象”等一些审音原则的看法,肯定了这么做的好处及贯彻这些原则时会碰到的问题。最后强调开展实际的方言调查,对于普通话审音工作的重要意义。
2.《音译词和意译词的消长》(1962)。这篇文章分析了清末至民国时期音译词和意译词的升沉消长,列举了币制、度量衡、职位称呼、社会称呼、实物、抽象概念等方面的词,并指出汉语吸收外来语词偏重意译,是民族语言本身的原因。这篇文章发表后,产生了较广泛的学术影响,多次为国内外同行引用。如美国学者麦卡斯基在他的《现代汉语中的印欧语借词:方法和问题》一文中多次引用我的研究成果。
3.《所字别义》(1979)。这篇文章是我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的代表作。该文分享了早些年北京口语里“所”字的一些特别用例,如“所是春天了”、“那事所是他做的”这类说法中的“所”字,指出这个“所”字是用在动词前起强调、加重的作用。文章还对这个词的历史线索进行了考察,指出北京话的“所是”源自元曲中的“索是”。文章将共时分析和历史溯源结合起来,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较早具有历史眼光的一次实践。王力先生赞许这篇近一万字的论文,“是以一个字为题材,写得很深入的典型”(王先生是我在西南联大的老师,对我的一点点有可取的地方,他也总是给予肯定)。
4.《酃县客家话的语法特点》(1988)。这篇文章是我在方言语法方面的试作。文章以我的母语酃县南乡山区客家话为考察对象,着重介绍它在语法方面的某些特点。词法方面,谈了名词词缀的特点和使根词生动化或强化的几种语音附加成分。句法方面,主要是谈助词的一些用法,包括个别副词和个别句式的特点。文章还归纳了这个方言的语音系统。20世纪80年代,方言学界对于方言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语音和词汇,研究方言语法的文章还不多见。这篇文章脱稿于我在20世纪30年代末写的《酃县客家方言》(未刊稿)的一部分,因此我对于方言语法的研究开始得还是比较早的。
5.《〈红楼梦〉词汇中的标音问题》(1986)。这篇文章集中讨论了编写《红楼梦语言词典》所遇到的词条注音问题,如“往这里来借宿一休”(六五回),“休”即现在的“宿”(xiŭ),词典则直音为xiū。文章论证了“一宿”那时是说成“一休”的。这篇文章较好地将词典条目的编撰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对于词典编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其他一些比较有分量的研究论文如:《〈红楼梦〉里的词尾“儿”和“子”》(1984),对《红楼梦》里这两个词尾的结构类型进行了全面分析,比较了二者构词功能上的差别,揭示了两百多年来这两个词尾在北京话里的某些变化,并讨论了“儿”“子”虚化的历史过程以及“儿化”的形成问题。《“挤对”和“挤兑”》(1984),对“挤对”和“挤兑”两个词的历史和使用上产生混淆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等等。
20世纪80年代后,我在词汇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红楼梦》这部专书展开的,在编写《红楼梦语言词典》的过程中,我陆续撰写了多篇《红楼梦》词汇考释的文章,例如《〈红楼梦〉词义演变一例》(1982)、《关于〈红楼梦〉中的“掌不住”》(1985)、《〈红楼梦〉的“茄鲞”一词辨正》(1991)等等。1995年,由我主编,钟兆华、白维国参编的《红楼梦语言词典》出版。这部词典共二百五十万字,收词二万五千余条,接近《红楼梦》词汇的总量。其中多数词条是语文性的,包括了许多虚词;少量是人名、地名、典章制度等词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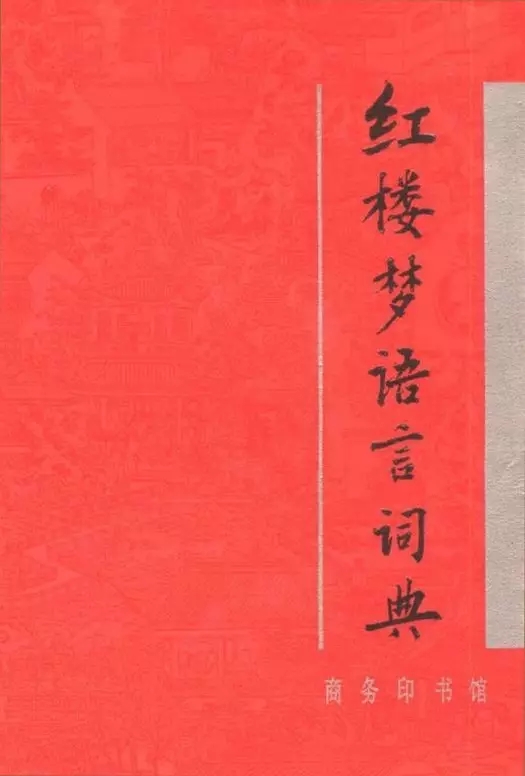
由于《红楼梦》被誉为“封建时代的百科全书”,它的词汇基本代表了18世纪北京话词汇的面貌,因此该词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18世纪北京话词典。读者可以通过词条和义项的比较,看出这一时期汉语词语同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异同,从而为研究汉语词汇发展提供了一个坐标。因此,它的出版被一些学者誉为汉语词汇史研究中的一个里程碑。新华社也对这部词典的问世用六种文字向海外数千家媒体刊发了消息。
20世纪50年代我编《中国语文》时,特辟“中国语言学史话”一栏,并带头撰写了《扬雄和他的〈方言〉》(1956)和《博闻强记的郭璞》(1956)两篇文章,用平易的语言介绍汉代扬雄和晋代郭璞的生平、著作及其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和影响。这个栏目后来得到海内外专家的支持和读者的欢迎,连续登了许多期。五六十年代,《中国语文》肩负着发展新中国语言学、普及语言知识、推动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以及促进汉语规范化等多重任务,我在主持编辑部日常工作期间,除了投入大量精力办好杂志外,还腾出时间写了《谈汉语规范化》(1955)、《语言科学在党的领导下向前迈进》(1957)、《努力发挥拼音字母对推广普通话和识字教育的作用》(1958)、《汉语语言科学的通俗普及工作》(1959)、《学习鲁迅,为汉语规范化而努力》(1961)等多篇文章,这些文章紧密配合我国语文工作的三大任务,积极推动语言科学的通俗普及,宣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语言科学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重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