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祖:说起《中国语文》杂志,我们知道,您是这份目前在国内外汉语学界有着重要影响的权威性刊物的最早创办人之一,还长期担任过常务编委,具体负责编辑部的日常工作,可以说,您为了它的成长壮大倾注了多年的心血。能不能请您进一步具体介绍一下您在《中国语文》杂志社工作时候的一些情形?
周:《中国语文》杂志是于1952年7月创刊的。编辑部由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人员组成,设在文改会内。那时文改会和教育部同在西单附近新皮库胡同的一个大院里,而语言所在东城王府大街的翠花胡同。每天我们语言所的几个人去文改会那里和郑林曦、曹伯韩、彭楚南等同志一起编这个杂志。1955年初,文改会迁到景山东街,编辑部和语言所就很近了。1955年底,杂志由语言所单独承办,编辑部也迁到语言所来,但编委会仍包括文改会的一些专家。这种合作关系一直延续到60年代初期逐渐改变编辑方针任务,并改单月刊为双月刊为止。杂志社设社长一名,由文改会副主任韦悫担任。编辑委员最初只有九人,后来逐渐增至三十二人,包括一些外地的,但实际发挥作用的常务编委会总共有十来个人,大约每隔两三个月开一次会,听取编辑部的汇报,商谈有关事宜。社长之外还设有总编辑,最早由所长罗常培先生担任,1955年4月改由文改会的林汉达继任。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后,总编辑一职无形中被取消,事实上总编的职责落在语言所领导(主要是吕叔湘先生)身上。
最初,《中国语文》是为了两项重要任务创办的,一项是研究和宣传文字改革,另一项是发展新中国的语言学。后者又要求兼顾普及语言知识和提高语言科学水平,因此凡是与语言有关的问题无所不谈,是名副其实的“杂志”。这样做的好处,是帮助语言学界从旧中国“不做或者反对所谓普及”,把语言学从只是“国家之崇尚学术”的“点缀”的狭隘状态中解脱出来,扩大了语言学领域和语言工作者的视野,而且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参加语言问题的讨论,他们中有不少人逐渐成为我国语言学的骨干力量。记得1956年在一次包括本刊编辑部负责人在内的小型座谈会上,中宣部周扬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搞编辑工作的要善于发现人才,帮助成长。有些人,就像一堆火在才开始冒烟,你扇它几下,就可能吐出火苗,越烧越旺;你不去扇它,就可能熄灭。搞编辑工作就要善于扇火。”他的这番话对于编辑部的同志,尤其是对我个人,很有鼓励和启示作用。
虽然给人的总体印象似乎是很杂,但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语文》还是比较集中地讨论过一些重要的语言学问题,例如1953年10月至1956年下半年由高名凯先生写的《关于汉语的词类分别》一文引起的关于汉语词类问题的讨论,其持续时间之长、参加争鸣的学者之众、讨论问题之深入、影响之深远,都是很有代表性的。
平心而论,50年代的《中国语文》在普及语文知识、参与社会“语言生活”,在贯彻国家语言政策,在促进新中国语言科学的发展、为日后深入研究开拓局面等方面是尽了力的。而且作者和读者较多,印数一度达到六万五千份。
《中国语文》创刊时,我被调到编辑部,其间因为工作需要曾离开过一段时间。1955年底,我重新回到编辑部,并负责编辑部的日常工作,直到1960年底才离开。那些年,我正当盛年,和编辑部的同志们一起,为编好这个杂志尽心尽职,为促进国家语言学事业的发展、增强语言学界的团结、贯彻国家语言文字政策,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祖:在您的求学和治学经历中,哪些人或事对您产生过大的影响?您的人生信条、做人的原则是什么?
周:我生平受罗常培先生的影响最深也最久。从大学二年级上他的音韵学课开始,到西南联大他指导我写作毕业论文,领我走上语言学之路,再到我在西南联大和北大教书,后又跟他一起调入语言所,直至他1958年逝世,许多年里我始终追随着他。罗先生对我的影响是全面的,从做学问到做人。虽然我资质驽钝,做不出罗先生那样大的学问,也没有走罗先生治音韵学的道路,但是他严谨的治学作风,深深地熏陶着我。我总是要求自己写文章要像罗先生一样严格,一丝不苟。要等资料积累够了,才能动手。要言之有物,不作空言,要言之有据,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要善于从剖析具体问题入手,步步为营,层层深入,穷究不舍,最终求得问题的完满解决,这便是罗先生教我的“抽丝剥茧法”。罗先生为人正直,待人宽厚而又疾恶如仇。记得反右运动中,所里有位“右派分子”自杀未遂,罗先生硬是冒着风险,亲自端着炖好的鸡汤去医院看望。罗先生脾气有时不大好,有一次我当面顶撞了他,但事后他也不以为忤,对我依然关爱有加。罗先生的这种是非分明的品格也深深地影响了我。
我在北大和西南联大求学期间,也受到过其他师长的影响。比如上面提到过的废名和杨振声先生,对我的文学创作很有影响。还有胡适先生,我虽然只在大一时上过他一年的课,没有多少私人接触,但他对各种思想一视同仁的包容态度,以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等治学格言却影响着我们一代人,非常了不起。还有魏建功、王力、唐兰、罗庸、沈兼士诸师,都是学问渊博、待人诚恳的学者,无论在专业上还是做人方面,对我都颇有影响。在西南联大,我有机会聆听到清华过来的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等先生的教诲。我上过闻先生的《诗经》《楚辞》,他的讲课始终充溢着一股深厚的爱国感情,感染着我们。我上过朱先生的“宋诗”,他的讲课风格平实,没有一丝江湖气。因为和别的课冲突,后来我退了朱先生的课,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对不起朱先生。朱先生却十分豁达,我毕业后,介绍我去中学教书的,就是朱先生。1948年听到朱先生病逝,我难过了好多天。我还旁听过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课,好像还发表过一篇《陈寅恪先生印象记》。这些北大之外的老师,拓宽了我的知识视野,使我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某种影响。
我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五四运动,但五四运动所宣传的民主、自由、科学的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却深刻地影响着我,成为我一生都恪守奉行的基本信念。在那些民生凋敝、国家垂亡的战乱岁月里,我一边钻研学问,矢志以知识报效国家,一边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很早便投身到抗日救亡、反对独裁的爱国学生运动中去。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我在上海浦东,跟着许多大中学生一起,跑到南京向政府请愿,要求出兵收复东北,结果被蒋介石亲自对我们的一通花言巧语骗回了上海。第二次再去南京游行,就不是请愿了,而是示威,结果被反动军警打落在水沟里头。1935年我上北大不久,“一 · 二九”运动爆发,我自始至终参与了这项运动,亲身感受了学生们高涨的爱国激情,亲眼目睹了反动军警残酷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甚至后来到西南联大教书了,还参加过许多次爱国民主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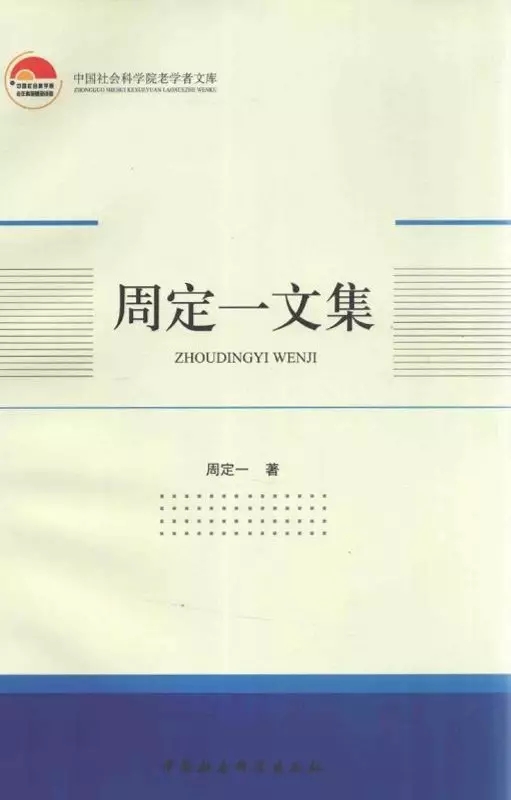
祖:请问您在治学方面最主要的体会是什么?您对本院乃至全国的青年学者有怎样的期望和忠告?
周:我是从教书转到搞研究上来的。教书需要的和搞研究大不相同:教书是现买现卖,是利用现有的成果;搞研究则一定要有自己的心得,要充分占有第一手资料。只有充分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你才能发现一些问题。发现问题以后,一定要穷追猛打,这样问题才能越想越明白,解决问题才越来越有希望。例如我写《所字别义》这篇文章,就是积累了很多材料的。初稿写成以后,也没有急着拿出来发表。是许多年以后,吕叔湘先生知道我有这么一篇文稿,遵照吕先生的建议才发表的。1979年,王力先生在给“文化大革命”后北大第一批汉语史研究生上论文写作课时,还特别以这篇文章作为例子:“最近一期的《中国语文》上,头一篇文章是周定一同志写的,题目叫《所字别义》。‘所’字的一种意义,别人不注意,没有讲到,他从现代北方话一直追溯到宋代,甚至追溯到先秦,写得很深入。这种文章值得提倡……”又说:“《所字别义》把人家没有讲到的那种意义的‘所’字能找到的都找出来,随时留意,做出札记或卡片。你别看写出来文章只有一万字,几千字,收集的材料却是几十万字。这叫作充分占有材料,材料越多越好。”事后我又发现了不少新材料。现在看起来,这篇文章需要修改的地方还很多,不过这个研究的过程和方法还是值得肯定的。还有《“挤对”和“挤兑”》《〈红楼梦〉里的词尾“儿”和“子”》《酃县客家话的语法特点》等论文也都是在积累了大量资料后才写成的。因为有了厚实的材料做支撑,所以文章就会言之有物。如果不是自己亲手摸材料得来的东西,只是利用别人的成果,这样的文章写得再长,也没多少价值。现在搞研究的手段比过去有很大的提高,年轻人更愿意利用电脑检索资料。这样做,的确是提高了效率,给研究工作带来了许多方便,但是绝不能完全用电脑代替人工,阅读原始材料的功夫可不能荒废。当然我这不是在鼓吹重走乾嘉诸老苦读经籍的老路,而是强调,在研究中我们可以利用电脑、工具书等去查找相关的研究线索,但到真正写作时,一定要核查原始资料,否则可能要闹笑话。话又说回来,搞语言研究,光靠资料积累还不行,还得有贯通资料的本领,要善于驾驭和组织资料,从中提炼出有价值的东西。有些人一辈子只会积累材料,不懂得贯通,结果只是做了书篓子。
我觉得搞研究工作,需要有一个安定、宽松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要有一股一条筋干到底的干劲儿,否则是无法做出什么成绩来的。这方面我是有体会的。我在到语言所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二十多年里,先后干过十多个部门的工作。就好像是挖井,一口井还没出水,又要你去挖另一口井。一个研究项目刚进行不久,一场政治运动一来,完了,只好中断了,事后又得重新来过。就这样折腾来折腾去,时间全都白白浪费了。这种教训是深刻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我开始决心研究《红楼梦》词汇,着手编纂《红楼梦语言词典》。从底本校勘开始,直到写成定稿,费时十数载,最后终于编成出版。如果没有这十年如一日的定劲儿,没有拨乱反正后语言所宽松的研究环境,仅凭两三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编出这等规模的词典来的。现在学术界有股浮躁的风气,害事得很。一些大学和研究部门也像催生婆一样,要求年轻人早出、快出成果。迫于形势,现在愿意坐冷板凳的青年人少了,急功近利、急于冒尖、投机取巧的人多了。这种学风很令人忧心。
现在学科分工越来越细了,年轻人需要掌握的专业知识越来越多了,学习的负担也越来越重了,因此妥善处理好博和专的关系也就显得越发的重要。我的大学启蒙老师胡适先生说过“为学要如金字塔,既能博大又能高。”这话很有道理。就是说专业基础要夯实,专业知识要广博,才能够出类拔萃。说到博,现在“国学”很时尚,“国学大师”多得很,很多人是懂一点古书,就自视为“国学大师”,实际连专家都称不上。但治学又不可以太专,不能把自己划在一个圈子里,搞语音的只管语音,搞词汇的只管词汇,搞语法的只搞语法;甚至于说搞语音的,只管某一时期甚或某部书的语音,就像王力先生曾经批评过:“有些学者光抱着一部书不放,别的书都不看。这怎么行?这本书是如何来的,源头如何?你不去摸它,颠来倒去,光是一部书,是不行的。”我觉得一辈子翻来覆去只研究一部书,虽然也能出些成绩,可到底是成不了大器。
祖:最后能否请您谈谈您目前的生活、工作状况以及您今后有怎样的计划安排?
周:我年事已高,精力也不比从前了。目前我每天除了坚持读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外,主要就是整理我的一些旧作,间或写点儿回忆文章。我还有一桩未了的任务,就是争取将罗常培先生的文集早日全部出版,告慰先生在天之灵。这部文集已经编了许多年,开始是因为经费问题,压在出版社那里很长时间。现在经费问题所里已经帮助解决了,却又因文集中大量的梵文、藏文材料一直没找到合适人选帮着校订,所以拖延至今也未得出齐。
(全文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