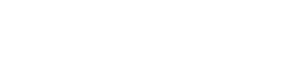曹剑芬:吴宗济先生学术思想简析
3.学术思想与理论体系

吴宗济先生学术思想的精粹,主要体现在对汉语元、辅音及音节的论述、协同发音理论、声调与语调思想、篇章韵律思想以及韵律处理模型等几个方面。
3.1 关于汉语元音、辅音及音节的生理和声学特性的论述
吴先生在国内首次系统地采用声学和生理测量的方法,通过对汉语普通话元音、辅音及声调的系统实验分析,揭示了汉语元音、辅音和声调的客观生理和声学特性,主要论述集中反映在以下几部专著和论文之中。
他与周殿福先生合著的《普通话发音图谱》一书,系统描述和介绍了普通话语音的发音生理,并给出了全部辅音、元音发音器官的X光照相、腭位照相和口形照相的综合图,是国内系统论述普通话语音生理特性的第一部专著。该书不仅为进一步的普通话语音生理特性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发音生理教学和语音矫治等应用领域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同时,作为该书成书基础的一大批实验数据和资料更为进一步的语音学理论探讨提供了系统的、不可多得(事实上是再也不可能获得)的生理实验根据。譬如,当国际著名语音学家拉迪福吉德(Peter Ladefoged)访问语音研究室时,看到《普通话发音图谱》一书以及这批实验资料时,简直是如获至宝,认为应该进一步发掘利用。于是,吴先生当即与他合作,通过对三位北京人的擦音与塞擦音资料(包括辅音、元音发音器官的X光照相、腭位照相和口形照相的综合图)的进一步分析,从不同语言的共性与个性的角度,从音系学跟语音学的不同角度,专门考察了辅音的“发音部位”这一特征。并且,很快就在国际语音学杂志上发表了“发音部位:一项对北京话擦音与塞擦音的调查”(Place of articulation:an investigation of Peking fricatives and affricatives, Journal of Phonetics,1984,12:267—278)一文。
他主编的《汉语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使用了当时国际上最新的语图仪记录分析了男女两人的发音,制作了普通话全部四声的单音节语图约三千幅,给出了音色、音高、音强、音长的声学参量,并附有六万字的总说明。是国内系统论述普通话语音声学特性的第一部专著。该书不仅为进一步的语音声学特性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普通话语音处理领域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根据和声学参数。
他与林茂灿先生共同主编的《实验语音学概要》一书,在介绍当时语音实验的最新方法和原理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研究成果,从实验的角度全面讨论了元音、辅音、声调、音节和音联、轻重音以及区别特征等方面的有关问题。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介绍实验语音学研究成果的专书,成为当时语音学和语音信号处理、言语工程学及言语病理学等专业研究生的热门参考书,1991年,荣获国家教委直属出版系统学术著作优秀奖。
此外,这一部分的论述还散见于许多单篇论文之中。除了早期的“普通话元音和辅音的频谱分析及共振峰的测算”和“一种分析语音的重要仪器——语图仪综述”介绍实验仪器和实验方法以及“实验语音学知识讲话”(《中国语文》1979年连载)专门讲普及知识之外,重点是深入论述辅音的特性。主要反映在“普通话辅音声学特征的几个问题”(与曹剑芬合作,在第二届全国声学学术会议上的报告,北京,1979年);“普通话辅音不送气/送气区别的实验研究”以及“普通话零声母音节起始段的声学分析”等多篇论文中。
3.2 关于汉语协同发音的理论
在中国语音学界,吴宗济先生首开协同发音研究的先河,通过对普通话不送气塞音和擦音音节内部及音节之间辅—元、元—辅音之间的协同发音考察,归纳出相关的声学模式,从发音生理上解释了汉语语音顺向或逆向的同化现象。同时,还运用协同发音原理解释汉语的连读变调现象。
首先,通过对普通话CVCV型双音节结构系统地声学分析和测量,他重点考察了普通话不送气塞音和清擦音跟相邻元音之间的协同发音现象。根据测得的元音共振峰目标值、辅音的VOT值、辅音的能量集中区和过渡音征等声学特征变量,他发现,就塞音音节组合而言,在音节内部,塞音跟后接元音之间主要是辅音受后接元音的同化作用;在音节之间,前音节元音常受后音节起首辅音的逆向协同发音作用,具体随辅音的发音部位而定。就清擦音音节组合而言,根据辅音与元音发音体的状态不同,清擦音的协同发音大约可分三类:
(1)同体同位的协同发音;(2)异体的协同发音;(3)同体异位的协同发音。
同时,他还运用协同发音原理解释连读变调现象,论述了字组中前音节被后音节同化后,前字调尾和后字调头音高特征的“顺势相连”“平滑过渡”规律,提出了音节间语音学变调的“跳板规则”。并以此拓展了赵元任关于三字组中首字为阴平或阳平时、次字阳平会变成阴平的理论,指出这里的次字阳平除了会变成阴平以外,还会变为类似去声的高降调,条件是:在双单格结构中,后字为阴平或去声(即高起的声调)时,中字阳平会变成高平,而当后字为阳平或上声(即低起的声调)时,则会变成高降。这个发现,不但充分揭示了普通话语流中阳平调型表现不太稳定的根源,而且为进一步探索连续话语中的声调变化规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基于上述协同发音理论,他不但为语音合成中音节之间过渡段的处理提供了理 论指导,而且还为语音合成系统的音段处理设计了规正方案。
这部分的论文主要有“普通话CVCV结构中不送气塞音协同发音的实验研究”“普通话清擦音协同发音的声学模式”和“普通话语音合成中协同发音音段变量的规正处理”等。
3.3 关于汉语的声调与语调思想
20世纪初期,刘复、赵元任两位语言学大师,开始用实验语音学方法对声调进行研究,主要采用浪纹计测算声调频率。赵元任先生在系统阐述汉语语调的定义、语调的类型以及语调和字调的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汉语的语调实际是词的或固有的字调和语调本身的代数和”是“小波浪加大波浪”的著名理论。吴宗济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师从赵元任先生,深得赵先生语调思想的熏陶。
从80年代开始,吴先生就从事普通话的变调研究。他继承并大大拓展了赵元任先生的汉语语调思想精髓,不但将赵先生提出的“橡皮条效应”以及“小波浪和大波浪”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量化,而且从语法、语音和音系三个层面考察语调的变化模式,提出了包括单字调、连调、变调、移调等“必然变调”规律和语气情态篇章语调的“或然变调”规律。
吴先生语调思想的精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3.1“必然变调”与“或然变调”
“必然变调”加“或然变调”是吴宗济先生语调思想的核心。
通常,汉语语调的“表层调形”复杂多样,以往的语音学家也曾试图把它们的调形曲拱归纳为有限的几种语气类型或模式,少则十数种(Chao, Y. R.,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多则数十种(Jing,S., 1992. The attitudes and intonation in Mandarin. 《中国语文》,第3期),相关的文献数以百计,但结论却大相径庭。
吴先生认为,汉语不同于西方的非声调语言,要认识汉语的语调特点,必须首先厘清语句中的声调变化。于是,便另辟蹊径,不走一般的归纳整体模型的途径,而是先从普通话的二字、三字和四字的连读变调入手,分析探索汉语语调的结构特点。
通过对普通话二字组、三字组和四字组连读变调的深入细致的实验分析,他发现,语句中的声调变化错综复杂,有的是“必然”的,是由发音生理、语法结构以及音系因素决定的“必然变调”;有的是“或然”的,是随语气及篇章等因素而定的“或然变调”。由于连续语言中的句子大都由若干短语或小句组成,一个句子的句调,不但混合着各种语音的、语法的和音系的必然变调,同时还融入了语气情态、轻重、节奏等等的影响所引起的或然变调。这就使得汉语语调的“表层调形”五花八门,很难归纳岀整体的模型和规则。因此,必须首先分清“表层调形”,从错综复杂的“表层调形”中“分滤”出哪些是语音、语法和音系因素决定的声调变化,怎样变化;哪些是语气情态因素引起的声调变化,怎样变化。
在实验分析的基础上,他归纳岀了汉语单字调和短语变调的若干相对稳定的模式,基本调型(basic contour),包括:单音节调型——“字调”(tone);多音节调型——“短语连读变调”(phrasal tone-sandhi)和取决于语气、轻重和节奏的“短语”连读调型(phrasal contour)。普通话的语调就是由这些基本调型组成。其中,“必然变调”的短语调形,即通常所说的连读变调模式,是句调中的“基本单元”,是构成语句语调的“底层调形”;而“句调”、即通常所说的语调,则是由这些基本单元通过“或然变调”组合而成的“表层调形”。因此,他认为,普通话的句调实际上是单字调、多字连读变调与句子语气变调的混合体。

3.3.2 字调与语调的关系
吴先生不但继承了赵元任先生关于字调和语调是“小波浪和大波浪”的“代数和”的著名理论,阐述了汉语声调与语调的关系,而且还进一步解析了单字调、多字连读变调怎样与句子语气变调叠加而成整句语调的原理。
他的实验分析进一步证实,汉语字调和语调的变化各有自己的规律。多字连读的“必然变调”主要是调形的变化,而跟语气语调相关的“或然变调”主要是基音音阶的迁移。因为字调是表义的,语句中的字调(包括词调)的调形变化必须遵循一定的“必然变调”规律,以确保其词义区别功能;而语调是表情的,主要通过调阶迁移来实现,是随语气情态的表达需要而定的“或然变调”。语句中的字调或词调“小波浪”,就是通过它们的调阶被语调“大波浪”托起或压低而“叠加”成表层的语调。
同时,他拓展了赵元任先生的语调思想,对赵先生提出的“橡皮条效应”以及“小波浪和大波浪”的“代数和关系”进行了具体的量化。语句中的字调在调阶受语调“大波浪”调节的同时,其调域的宽窄也随轻重或节奏的变化而会被扩展或压缩。不过,究竟怎样展缩?不同语调展缩多少?在赵先生那时的条件下还难以解决。而吴先生通过深入细致的实验证明,语句中的调域大小虽然因人而异、因语气而异,但是,其规则是可以预知的。他创建了把基频频率转换为半音的方法,提出了实现从“底层调形”到“表层调形”的一系列转换规则。
3.3.3 从频率值到半音值的转换方法
众所周知,自然话语中声调和语调的绝对音高和频率范围,不但因人而异,而且因为语气情态的变化,即使同一个人话语中的绝对音高和频率范围也会引起巨大的差异。这是存在于汉语语调研究中的一大障碍,更是困扰语音处理的巨大难题。实际上,这就是怎样认识和量化处理“橡皮条效应”和“代数和关系”的问题。
吴先生基于赵先生关于“四声调值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性的绝对值,而是对数的相对值,也就是音乐性的旋律值”的理论以及他不用频率、而用十二平均律的半音音程来记调的方法,结合乐律原理,提出了从基频频率到半音音值的转换方法。因为不同语气的语句中的基调变化多端,若以频率赫兹值为标度衡量其移动等级,差别会很大;如果把赫兹标度换算为乐律的音程或半音程标度,语句中各短语移调后,基调虽有了变动,而调域宽度的音程是相等的。因此,这个方法的提出,不仅使得客观声学参量的描述更加符合人的听觉感知特性,而且为语音学者和言语工程学者度量和处理语句中的声调变化提供了有效的量化手段。更主要的是,这种转换方法的提出和应用,为进一步探索自然言语中从“底层调形”到“表层调形”的实现方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