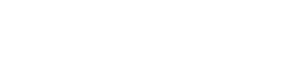曹剑芬:吴宗济先生学术思想简析
3.3.4 句中短语调域及音阶移动的“移调规则”
探索自然言语中从“底层调形”到“表层调形”的实现方式,实质上就是探讨怎样从赵元任所说的从中性语调到感情语调的转换原理。
连续话语中的语句,除了短语内部的“必然变调”,还有来自语气(例如疑问、祈使)变化和语境(例如逻辑或感情重音)影响而产生的“或然变调”。因此,实际话语中句子的“表层调形”已经偏离“底层调形”甚远。仅从复杂多变的表层表象很难认清“底层调形”是怎样实现为“表层调形”的。为此,吴先生采取了抽丝剥茧的办法,层层深入,揭示岀“调位守恒”“移调”“变域”“韵律互补”等一系列规则。解决了赵元任当年“暂时没有想出好法子”的难题。
首先,通过对不同语境中选取的具有不同语气语句的深入分析,他发现了不同短语调群的调域基本守恒的特性。具体地说,从对句中基本调群单元的调域和音阶的集中分析结果来看,自然语句中有些短语调群的调形曲线虽然会随着语句表达的变化而上升或下降,但是其调形模式却与正常状态时差不多。尤其是把基频的绝对频率值转换成乐律的半音标度以后,所有调群的调域相互之间非常一致。
其次,从对语调的基本单元及其组合形式的具体分析发现,调群的调形曲线的上升或下降主要是音阶运动引起的。这就意味着,句子中短语的调形可以在不同的音阶条件下实现而不失其一致性。就像乐曲中乐句的旋律可以用不同的基调来演奏却仍然保持着主旋律那样,言语中某个调域内的任一短语调形或调位都可以在另一个调域中使用,其音阶虽然随着不同语气的语调而改变,但其区别词义的功能并不改变。由此他认为,言语中的局部调形的调域和音阶的变化,犹如乐曲旋律的“移调”或“转调”(change key),自然言语中从“底层调形”到“表层调形”的实现也是遵从“移调规则”的。因此,在语音处理上,他主张采用乐律上的“移调”原理来量化语句中短语调域和音阶(即调阶)的变化。此外,还发现,由于实现过程中还涉及由轻重和节奏变化引起的调域的扩展或收缩。所以,在移调的同时,还会产生“韵律互补”和规律性的“变域”。
基于上述发现,吴先生还建立了从中性语调到感情语调的转换模型。通过移调处理,就可以从一个平叙句的短语调形生成出各种具有不同语气的基本调群,从而实现从中性语调到感情语调的转换。
3.3.5 “跳板规则”“多米诺规则”和“极化规则”
在对语句的“底层调形”到“表层调形”的分析过程中,吴先生还注意到,语句中的声调变化除了遵从“移调规则”以外,还遵从另外一些影响基本单元内部变调以及因语气变化引起短语调形抬高或降低的外加规则。例如,短语在句子中,由于连音的依存与制约而产生“必然变调”,其变化方式和规律可以归纳为“跳板规则”“多米诺规则”和“极化规则”。
“跳板规则”是从音节间语音学变调的过渡分析中归纳得出的。它是由“语音学”的协同发音决定的一种必然变调规则。譬如,以三字组的变调为例,次字的调形夹在首字的调尾与末字的调头中间,前后被同化而成为过渡调。这种过渡调就像两头分别搭在船舷与岸边的一条跳板,正如跳板的斜度会随着潮汐的起落而改变一样,这种过渡调的斜度也会随着首字调尾与末字调头的不同而改变。这一规则适用于所有音节间语音学变调的过渡分析。
“多米诺规则”(domino rule)是取决于语法结构的直接成分优先变调规则。在对三字以上字组的变调分析中他发现,有时,同样是四字组,但变调模式却不同。究其原因,跟它们的底层语法结构的不同有关。根据其底层结构(并列结构除外),总是先从其中的二字直接成分形成一级连读变调,然后,再跟其余的字调发生同化或异化,构成二级变调。字数愈多,层级就愈多。
“极化规则”(polarization rule)是指“音系学”的历时音系的极化变调。例如,普通话里两上相连,第一个上声不按一般的协同发音的逆同化规律变为“半上”,而是按音系学的“逆异化”规律变成同阳平相似的调型。
3.3.6 语音与语法相结合的语调分析方法
为了发展和完善语调研究,吴先生特别重视语音与语法的结合。这首先表现在他对普通话三字以上字组变调的分析中(“普通话三字组变调规律”英文本,1983,第十届国际语音科学会议论文集),指出它除了以双字组变调规律为基础之外,还有些取决于其本身语法结构的变调规律。对此,大家都已很熟悉,这里不再赘述。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他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解决了汉语语音韵律分析的难题”一文中,灵活运用语法上的层次结构分析法,通过厘清底层语音单元的特性及其变化规律,来解析语音韵律的表层现象,从而解决了汉语语音韵律分析的难题。由于该文发表于他的文集出版之后,一些读者可能尚未有机会拜读,这里略引一二,以飨读者。
(1)受吕叔湘先生关于“词,短语,包括主谓短语,都是语言的静态单位,备用单位;而句子则是语言的动态单位,使用单位”的语法思想的启发,认识到自己原先把最小单元的恒定变调调型叫做“必然变调”的,实际就是“静态单位”;而把多变的语调叫做“或然变调”的,实际就是“动态单位”。于是,就想到有可能把一切短语的变调现象,都作为“备用”而编成固定(静态)的程序即时调用,再无须去一一计算,这样就可以在工程上节约大量人力、物力。而语调既然是动态的,是随“使用”而变的,就得另立规则。
(2)根据吕叔湘先生关于语言的“结构层次”的思想(任何一个语言片段都是由若干语素构成的,但不是一次组成,……而是一层一层组织起来的。因此,拿一个现成的片段来分析,总是先一分为二,然后一层一层分下去,分到全部都是单个语素为止……,叫做“直接成分分析法”,非正式叫做“二分法”,其实也不一定是二分,比如遇到并列的三项,就只能三分了),认识到再复杂的语调只要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对它“顺藤摸瓜”,就能理清每个语调的“直接成分”。因而想到在言语工程上干脆以“直接成分”为句子的最小处理单位,可给语音处理极大的便利。联系到他之前关于四字组的变调分析,认为四字以上的短语表层变调是个混合体,绝不是所谓的“语调模型”。分析时就先以最底层的短语变调模型为基本单元,是第一次变调;其前面最接近的音节首先被逆同化而变调,这是第二次变调;再前面的音节又被逆同化而变调,这是第三次变调,……这依次递进的变调在口语中都是不假思索、必然产生的,然后最终变成表层语调。这种逐级变调的程序是连锁式的,可比照“多米诺”骨牌效应把它命名为“多米诺规则”(“普通话韵律变量的处理规则”,1984;“普通话语调规则”,1988)。……这类变调遇到全为上声时,……由于上声有三种变体(两上连读,前上变阳平;上连非上,前上变半上;上声重读时,保持全上),因而不同的语法结构就有不同的表层调型。……如不用“多米诺规则”是无法分析清楚的。用“多米诺规则”处理变调正是“直接成分分析法”的“回归处理”,……这在言语工程中的应用上已起了不小的作用(“直接成分分析法”为语调分析的“多米诺规则”提供了理论基础,为处理复杂多变的“多字组”变调的难题,铺出了事半而功倍的坦途)。此两概念被今日言语工程界直接或间接应用而受益者已不止一家。
3.4 关于篇章韵律的论述
吴宗济先生在实验研究中发现,语句的韵律不单和“语音”“语法”“音系”有关,更和“语义”“语用”的环境有关。因此,不能离开语言环境而孤立地去分析句子的韵律。所以,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他以愤怒兼命令的感情句为例,对情感语调和篇章韵律的声学表现进行了探索。他发现篇章中短语的移调程度和扩域程度受到语体的制约,而服从篇章韵律的规则,表达逻辑重音和感情重音的任务、已基本上由代词、副词承担,而使名词和形容词的韵律变量相当降低了。
他的实验结果还表明,声调、重音和时长是构成语音韵律的三项特征,三者之中最起作用的是声调,其变化规律也最繁。重音的物理量主要是声音的强度,但听感上的强弱,却在于三者的相互搭配所起的作用。有两种现象是过去不大注意的,但却与语音的自然度有关。一是声音的延长也能代替声调的提高而起加重语气的作用;二是音量加重(用力)时,音调就必然会同时升高。二者的关系是密切的,但不能逆转,提高声调就不一定要加强音量。在这里,吴先生的主要意图在于说明音高、音长和音强是构成韵律特征的主要声学参量,重音作为听感上的强弱,同样跟时长和音高具有密切的关系。
此外,吴先生还对篇章韵律跟书法、绘画等其他艺术表达手段的共同特性加以探索。通过多方面的观察分析,他认为,“能够高度自然表达思想的媒体:在书法为‘草书’,尤其是‘狂草’;在画法为‘水墨’,尤其是‘写意’;在话法则为口语,尤其是表情的语调(广义的语调就是‘韵律’,也即‘高低’‘轻重’和‘长短’三种特征的综合)。”
例如,在“‘书话同源’——试论草书书法与语调规则的关系”一文中,探讨了草书运笔与文字的语法结构的关系,发现草书的书法跟汉语声调变化的规律,在语法关系上几乎完全一致。
从诸家草书中,他把草书的“书法”和言语的“话法”的关系总结为三条规则:
(1)草书(特别是狂草)中凡遇到语法上的“直接成分”(词或短语),少则两字,多则整句(只要不受纸张轮廓的限制),基本上都用连绵或映带的笔法;而且上下字相接时的字形过渡,主要是逆向的同化。(即上字尾笔多半为了“俯就”下字的起笔而变形、移位,并加上一段过渡的笔画;但下字的间架基本保持稳态,只是为了“仰接”过渡段而使起笔有了一些变化。所谓“一字之末,成次字之首”。)
(2)狂草运笔中,凡是遇有“逻辑”上或“感情”上须要强调或弱化某些短语或词句时,就常用“跌宕”或“错综”的笔法来表达。即强调时将字形放大,或再将行款作倾斜或出格的移动;弱化时把间架缩小,或把点画简化。
(3)上述规则在两字连接时,下字的点画和间架基本上是稳定的。但如遇有多字须要一气连接时,中间的字形就有可能因承上启下,而把点画间架用轻笔加以简化或变形。
而草书的这些规则无不与话语语调变化规则相通。所以,他把草书的连写运笔规则和语调的连读变调规则的共通性做了高度概括,对照总结为:
草书 语调
“执”:字型的深浅长短 调型的高低升降
“使”:走势的纵横牵掣 过渡的同化异化
“转”:连笔的钩环盘纡 连调的断续蜿蜒
“用”:气韵的点画向背 韵律的轻重疾徐
3.5 关于语音学在语言教学和言语科技工程中的应用研究
吴宗济先生一向注重语音学理论研究与语言教学和言语科学技术研究的有机结合,尤其是近十多年来,特别致力于语音学理论在语音合成中的应用研究。
在语言教学方面,他与赵金铭等合编的《现代汉语语音概要》,在介绍语音学的基础知识和现代汉语语音系统的同时,充分融进了他在汉语语音变化及声调变化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是一部适用于中外学生学习,尤其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优秀教材。
在语音学用于言语工程中的应用研究方面,他更是呕心沥血,针对语音处理需要以及汉语的语音特点,同时吸收和继承了中国音韵学的精华,亲自为语音合成设计了一系列的音段和超音段的处理规则和模型。例如,基于他的协同发音理论,不但为语音合成中音节之间过渡段的处理提供了理论指导,而且还提出了处理中的规正方案。按照普通话单字可能的元音和辅音字首和字尾,两字连读后可构成二百九十七种辅—元或元—辅之间的过渡状态。若每种状态都给岀模式,必将造成处理上的困难。而根据协同发音原理和相关的实验,他把相似或相近的声学模式加以归类和精简,最后只要用十一种过渡模式,就能应用于全部二百九十七种组合了。他提出的这个规正方案对合成系统有很大的简化作用,已被多处引用。又如,根据汉语单字调和短语变调特点,比照音乐的乐理,他制定出汉语因语气变化而引起的短语调抬高或降低的移调处理规则以及短语调之间相互联结的跳板规则和多米诺规则等外加规则,并进而为改进合成普通话口语的自然度设计了全面的韵律处理规则和模型。这些处理规则和模型已被相关方面如中国科技大学及清华大学应用于语音合成系统的设计和改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这部分的论述集中体现在他关于语句中的声调变化(包括从二字组到四字组的变调规律)、汉语普通话语调的基本调型、语调规则以及语调处理方法等十几篇论文中,占了他的《论文集》的半数,此处就不一一列举了。
4.简要评述
吴宗济先生的学术思想内涵深广,绝不是这篇小文的简析所能涵盖的。以我个人的理解,吴先生对于中国语音学的贡献,首先在于系统地采用声学和生理测量的方法,揭示了汉语元音、辅音和声调的客观生理和声学特性,从而推动了实验语音学在中国的发展;第二,首开中国协同发音研究的先河,建立了汉语语音研究跟言语产生理论探索的初步联系;第三,更为重要的是,在汉语语调研究领域,吴先生的研究更具开创意义。因为自赵元任先生之后,汉语在语调研究方面曾经出现了一段空白,是吴先生的研究续上了这段香火。他对汉语语句中的声调变化的深入分析考察,开创了汉语语调研究的新局面。
在汉语语调研究方面,是赵元任先生首先揭开了汉语语调不同于英语等西方语言语调的面纱,而吴宗济先生正是循着赵先生的学术理念,实实在在通过对声调和连读变调到句调的系统扎实的实验研究,带领中国语言学界走出了那条要么简单地生搬硬套植根于西方语言的语调模式、要么认为“汉语没有语调”的死胡同。这种观念上的转变和行动上的实施实质上无异于一场革命。因此,其开创性和奠基性是显而易见的。
关于汉语的声调和语调理论及其在语音合成中应用的韵律模型是吴先生学术思想的核心。如果说赵先生的声调和语调理论本质上还是定性描述的话,那么,吴先生对汉语语调的探索已经是定性和定量兼备了,他所建立的一些处理规则和应用韵律模型已被相关方面如中国科技大学及清华大学应用于语音合成系统的设计和改进。这些规则和模型所发挥的作用堪与赵元任先生发明五度制的贡献相比。
吴先生的研究大大推动了汉语语调的研究,提升了汉语语调理论水平,乃至中国现代语音学的理论水平。正因为如此,吴先生不仅是中国语音学界的泰斗,而且享誉国际语音学界。如果说,是赵元任、刘复等先辈在中国土地上播下了科学语音学的种子,那么,正是吴先生的不懈努力和卓越贡献,使中国几经劫难的科学语音学的“香火”得以继续,并引领这个学科坚持走基础理论研究跟实际应用紧密结合之路,不但迎来了中国语音学蓬勃发展的春天,而且丰富了世界语音学的宝库。正如美国著名语音学家J. Ohala教授曾经指出的那样,吴先生的研究提升了国际上对汉语声调、辅音和元音以及韵律的理解,不愧是新兴一代追求科学地认识言语的语音学家的楷模(J. Ohala,2004)。

1978年,吴先生(左前)在第九届国际语音科学会议上与Fromkin
教授、Stevens教授(左后)及Fant教授(右后)讨论
综上所述,吴先生对汉语语调的这些细致扎实的研究和探索,为我们今后进一步深化汉语“一地一个样子的”中性语调研究、探讨语句中韵律短语音高曲拱复杂多变的本质特性及其语境变化规律、从而攻克汉语语调结构研究的难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5.参考文献
(注:凡已收入《吴宗济语言学论文集》的论文,此处不再单列)
[1]吴宗济 1938 调查西南民族语言管见,《西南边疆》第1期。
[2]赵元任、丁声树、吴宗济等 1948 《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商务印书馆。
[3]吴宗济 1958 武鸣壮语中汉语借字的音韵系统,《语言研究》第3期。
[4]吴宗济(用齐鲁笔名) 1961 谈谈现代语音实验方法,《中国语文》第10、11期合刊和第12期连载。
[5]周殿福、吴宗济 1963 《普通话发音图谱》,商务印书馆。
[6]赵元任、丁声树、吴宗济等 1974 《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中研院”史语所。
[7]吴宗济等(用余音士笔名) 1979 实验语音学知识讲话,《中国语文》第1至6期连载。
[8]吴宗济 1986 《汉语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9]吴宗济、林茂灿 1989 《实验语音学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
[10]吴宗济 2004《吴宗济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11]吴宗济 2010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解决了汉语语音韵律分析的难题,收入《吕叔湘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商务印书馆。
[12] Ohala,J. 2004. A Role of Model for Scientific Phonetics, Messages of Congratulations to Professor Wu. In G. Fant,H. Fujisaki,J. Cao & Y. Xu(ed.), From Traditional Phonology to Modern Speech Process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作者简介:

曹剑芬
196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同年8月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64-1975在二组(今方言研究室)工作;1975-1976年借调到词典室参加《现代汉语词典》修订工作;1976年调到三组(现语音研究室前身)从事语音实验研究,直至1998年9月退休。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实研、助研、副研和正研,IBM中国研究中心语音部顾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曾兼任中国声学学会语言、听觉和音乐声学分会委员,中国语言学会语音学分会委员,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语音信息处理专业委员会委员,香港新时代国际文化出版社科技专家顾问。现兼任中国语言学会语音学分会顾问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现代语音学和方言音韵,主要从事现代语音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和计算机自然语音处理的应用基础研究。先后参与了国家社科七五、八五和九五重点项目、国家高科技八六三项目以及两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集体项目的工作。单独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普通话正常重音音节间音联特性研究”和十个社科院老年科研基金资助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