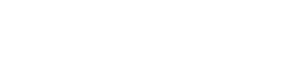吴福祥研究员访谈
张定:您在做汉语历史语法的同时,也做了一些方言语法史和南方民族语言语法演变的研究。您如何看待这几个领域之间的联系?有没有什么外在的因素促成了这种研究范围的延伸?
吴福祥:近些年,我在做汉语历史语法的同时,也涉及汉语方言特别是南方方言语法史的研究。不过,我研究方言语法史,着眼的并不是汉语历史语法和现代方言语法的古今印证,而是力求将现代汉语方言语法史作为一个具有独立地位的本体性研究对象,换言之,我主张汉语方言(尤其是南方方言)语法史是汉语语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正如梅祖麟先生所指出的,我们迄今所做的汉语语法史研究,主要是官话方言的语法史研究。显而易见,这种研究框架是不全面的,不能完全反映汉语语法演变的模式和规律。所以近年来我一直呼吁,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应该将基于历史文献的研究和基于方言比较的研究结合起来。
至于我做南方民族语言语法演变的研究,我认为我仍然是在做语法化和历史句法的研究,只不过使用的语言材料或选取的对象语言有所不同而已,这些研究都属于历史句法学。这就好比植物学家在从事植物学研究时既可以以中国黄山的植物为标本,也可以以亚马逊热带雨林的植物为标本。这也就是刘丹青教授以前所说的语言学研究中学科导向和语种导向之别。
细想起来,我后来将研究范围延伸到汉语方言语法史和南方民族语言语法演变,应该与柯理思教授的影响分不开。1996年5月,我应贝罗贝教授的邀请访问法国科研中心东亚语言研究所。在巴黎期间,我和正在巴黎休假的东京大学教授柯理思女士讨论学术时,对方作为一位外国学者,对汉语方言语法了如指掌,而我一个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学者却常常一问三不知,当时我真恨不得立刻找个地缝钻进去。回国后,我就开始系统地阅读方言研究文献。当时我注意到,国内做方言语法的学者,要么是方言学的出身,要么是现代汉语语法的背景,他们大都将所描写的方言语法现象视为共时的状态;而我们做历史语法出身的人因为有历时视角和历史语法的训练,很容易透过那些共时状态窥见其间的历时关联和演变过程。
2002年,我去日本东京大学访问,柯理思教授送给我刚出版的Thomason的名著《语言接触导论》(2001)。读完这本书特别是Thomason和Kaufman的历史语言学名著《语言接触、克里奥尔语化和发生学语言学》(1988)后,才知道语言的演变有“语言内部因素促动的演变”和“语言接触引发的演变”两类,而我们以前的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基本上只做了一半的工作,因为接触引发的语法演变我们以往基本上没有涉及。后来读到Heine&Kuteva(2003,2005),就觉得他们的“语法复制”(grammatical replication )模型似乎更具有操作性,于是就想做一点接触引发的语法演变的研究。可是,汉语史中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因为时过境迁,我们对其社会语言学情景(sociolinguistic situation)难以直接观察,因此很难找到特别有力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结论都只能是或然的。于是就想到,不如做一点南方民族语言接触引发的语法演变的研究,因为这些接触性演变正在发生,我们对其演变的社会语言学情景可以做一些在线观察和研究。

吴福祥著《敦煌变文语法研究》(岳麓书社,1996年)封面
张定:在您的语法化研究中,几乎随处可见语言类型学的影响。您觉得两者有哪些相通之处?
吴福祥:语法化与语言类型学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首先,二者在语言观和基本假设上多有相似之处,比如它们似乎都主张:(a) 语法结构和语法演变导源于语言使用,因此“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或“语言能力”(competence)与“语言运用”(performance)之间并非截然对立,而是一种共生(symbiotic)和互动(interactive)关系;(b) 语言的信递(communication)功能及与之相关的语用原则是解释语言结构和语言演变的主要维度或参数;(c) 语言的共时状态是历时演变的结果,共时和历时只是语言研究的两个视角(perspectives),并非语言本身的两个平面;(d) 语言并非自足的,它跟语言之外的认知、语用和社会因素都密不可分;(e) 语言范畴具有非离散性,即语言中建立的各种范畴具有连续统性质,其间并没有清楚的边界。实际上,上述这些观念或观点不仅仅为语法化与语言类型学所独有,也是功能主义语言学其他流派(如认知语言学、语用学、话语语言学)所共同主张的,正因为如此,语法化与语言类型学通常被视为功能主义语言学流派或者叫做功能-类型学流派,以跟形式主义流派相对待。其次,在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上二者也多有交集和叠合,比如语法化有一种研究范式叫做“共时语法化研究”,其重要的研究课题是人类语言中什么样的语义、话语-语用功能在语法系统中被编码以及同样的语义、话语-语用范畴在不同语言中以什么方式来编码,而这些问题恰好也是语言类型学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语言类型学中有一种“历时类型学”( diachronic typology )研究范式,也称“共时类型学的动态化”(the dynamicization of synchronic typology),其主要目标是研究语言演变(特别是语法和语义)的共性和制约,而这正是语法化关注的焦点。正因为如此,William Croft《语言类型学与语言共性》(2003)第八章在论述历时类型学时实际上主要是在谈语法化问题。还有一个现象也可看出语法化与语言类型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国外很多知名的语言类型学家同时也是卓有建树的语法化学家,比如Joseph H. Greenberg、Bernard Comrie、William Croft、Martin Haspelmath、Östen Dahl;同样,有些杰出的语法化学家同时也是造诣甚深的类型学家,如Talmy Givón、Christian Lehmann、Elizabeth C. Traugott和Bernd Heine等等;至于著名语言学家Joan Bybee,实在很难说她到底是语法化学家还是类型学家。